狂喜过后-杜甫“蛟龙无定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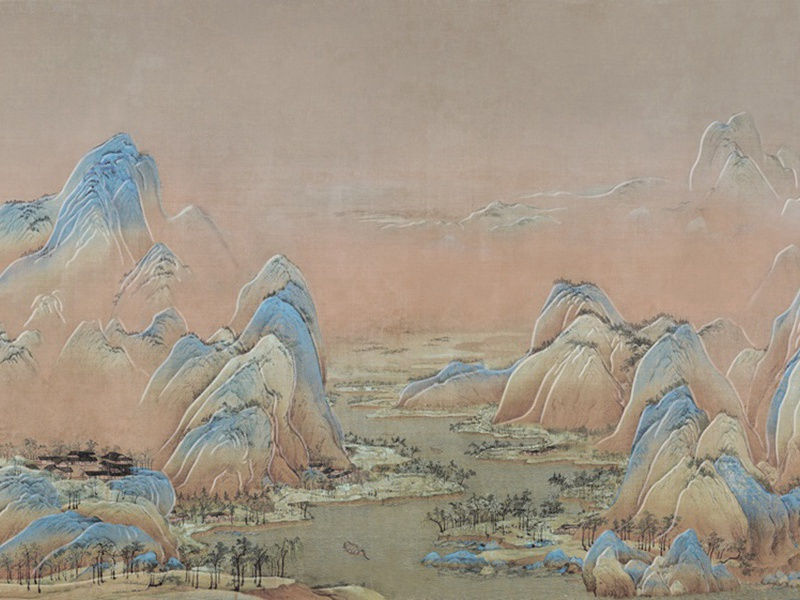
这一年,老杜主要是在梓州度过的。
开春,老杜一听到史朝义自缢、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喜讯,真是欢喜欲狂,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说: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头年(宝应元年)十月,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统兵十余万,进讨史朝义,收复洛阳。老杜当时在梓州闻讯,曾作《渔阳》一诗,讽叛党归顺,慰燕人向化说:“渔阳突骑犹精锐,赫赫雍王都节制。猛将翻然恐后时,本朝不入非高计。禄山北筑雄武城,旧防败走归其营。系书请问燕耆旧,今日何须十万兵!”渔阳的突击轻骑虽还精锐(1),可是怎敌得住由威名赫赫的雍王(即德宗)统领的大军。河北诸将翻然来降犹恐后时,你们若再不归附本朝那真是失策。当初安禄山筑雄武城(在范阳北),以防战败有所退守。我想捎个信请问燕地父老:如今这样的形势不须十万兵马来收拾那些负隅顽抗之敌人吧!——可见老杜虽远在剑外,对中原战局还是很了解(他经常与当地官员交往,消息当然比较灵通),对直捣叛军巢穴也是很有信心的。而且年初史朝义战败北走之事他也偶有所闻,曾志之于诗:“贱子何人记,迷方着处家。竹风连野色,江沫拥春沙。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似闻胡骑走,失喜问京华。”(《远游》)虽然如此,一旦得知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成了事实时,他仍然会感到喜出望外,会惊喜若狂的。开心就笑伤心就哭,这是人之常情。但在特殊情况下,哭也能倾泻人们内心的巨大惊喜。当人们忽然遭到巨大惊喜的袭击时,往往是不会笑的;如果大笑,倒是反常现象。这时只有那倾盆大雨似的滚滚热泪直流,才能发泄得出这种强烈的感情。何况诗人这滚滚热泪中,还饱含着往日因战乱而忧国忧民的痛苦,和流离失所、辗转道路的辛酸。随着激情得到尽情宣泄,他稍为平静些了,他定了定神,原来他的妻子儿女都在身边,个个喜形于色,往日那满布在他们脸上的愁云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了。这时一个多年积压在内心深处的念头突然涌现了出来:“余田园在东京”(篇末原注),我真想马上结束这长期痛苦的流浪生活,回老家去安居乐业啊!在这样一个强烈念头的冲击下,他又沉入了兴奋状态中。当他看到房里到处散乱地放着打开的书卷,就把它卷起来,收拾好,准备要走。想走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走得了的,无须马上急着收拾东西,这不过是他“喜欲狂”时的一种下意识动作而已。所以说是“漫卷”,就是不经意的意思。这样写真好,不仅生动地传出了他当时那种乐不可支的神情,巧妙地表达出他内心的无限喜悦,而且还反衬出刚才听到喜讯之前他客居无聊、以诗书吟咏遣愁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
庾信《拟咏怀》其十八有这样两句诗:“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也是借满屋的琴声、满床的书卷来衬托作者“中夜忽然愁”的无穷愁思,可参看。诗人越想越兴奋,不禁放声高唱起来,还要借酒来表达他满怀的欢乐。想到现在严冬已经过去,春光明媚,正好和难友们结伴回乡,就更加心旷神怡了。黄生说:“‘青春作伴’四字尤妙,盖言一路花明柳媚,还乡之际更不寂寞。四字人演作一联,未必能佳也。”“白日”“青春”,这是多么富于展望的字眼!诗人一直生活在苦难的战乱年代,就像生活在阴沉的严冬季节一样。今天获得最后胜利的喜讯,正如一声春雷惊破了漫天的云雾而重现出春日的阳光。在这春天灿烂阳光的普照下,万物欣欣向荣,长期心情抑郁的人们也顿时感到胸襟豁然开朗,重新燃烧起心中久已熄灭的希望的火花,在具体地做还乡的打算了。“放歌”“纵酒”都是语气很重的字眼,“须”字也一样。用这样些明快而果断的语言来写当时那种极端喜悦而豪迈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了。在阳光普照的“白日”,他“放歌”他“纵酒”,这可说是他长期苦闷抑郁心情的一次大解放。感情充沛,表现得也很有力量。想到在这美丽的青春季节,与人结伴回各自的长期阔别、梦魂萦绕的家乡,不觉一往情深,语气就显得格外亲切了。长江自巫山入巴东为巴峡,在湖北巴东县西二十里。三峡中最长的是巫峡。巫峡首尾一百六十里,因巫山得名,在四川巫山县东。老杜自蜀还洛,顺长江而下,理应先经巫峡而后经巴峡。注家见“即从巴峡穿巫峡”悖于常识,就认为这“巴峡”指的是巴县(今四川重庆市)一带江峡的总称(有的更引《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巴县以东也有明月峡等三峡为证),非巴东县西的那个巴峡。这样,解释起来就顺理成章了。林庚先生考之最确:“‘巴峡’,四川东北部巴江中的峡。《太平御览》卷六五引《三巴记》曰:‘阆、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涪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采此说)廖仲安先生则认为:“渝州以下之川东峡江地带,均可称‘巴峡’。观戎昱《云安阻雨》诗‘日长巴峡雨濛濛’,称云安为巴峡;白居易在忠州有诗题云《木莲树生巴峡山谷间……忠州西北十里有鸣玉溪生者秾茂尤异……因题三绝句云》,则称忠州为巴峡;杜甫《八哀诗》(李光弼)云:‘疲苶竟何人,洒涕巴东峡。’则夔州亦可称‘巴峡’。”说亦有据。不过,我倒觉得这“巴峡”还是理解为指巴峡县西的那个巴峡为好。(一)巴县以东明月峡等并无作为总称的“巴峡”这个地名。固然老杜也可以将“巴东明月诸峡”简化成“巴峡”,但尾联“巫峡”“襄阳”“洛阳”都是实有的专用地名,怎好在前面加一个自拟的泛指地名呢?(二)虽说诗人这几年来早就琢磨过这条自蜀还洛的最佳路线,对沿途埠头也应有所了解,但处在闻捷狂喜的激动之中,他只想到过了这四个地方就可到家,即兴吟诗,一时把沿途必经的两个地点前后弄颠倒了,也是完全可能的。老杜事后之所以不改(要改也很容易,“巴”“巫”皆平声,只需将此二字易位即得),兴许认为这个偶然的疏忽,恰好最能表现当时那种“喜欲狂”的神情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李白《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从白帝城到江陵,走的就是“从巴峡穿巫峡”的水路。在长江上游顺水行舟确乎神速,但水流之速、舟行之速终赶不上诗人归心之速。“巴峡”“巫峡”“襄阳”“洛阳”是沿途相距不近的四个地点。诗人标出它们,然后用“即从”“穿”“便下”“向”这样一些表示快速的字眼将它们串联起来,就不仅从意思上,也从急促的节奏上将行旅的神速和渴望还乡心情的急迫表现出来了。可叹的是,他的这个叶落归根的心愿是永远不能实现了。这是他的悲哀,这是时代的悲哀!顾宸说:“杜诗之妙,有以命意胜者,有以篇法胜者,有以俚质胜者,有以仓卒造状胜者。此诗之‘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于仓卒间写出欲歌欲哭之状,使人千载如见。”王嗣奭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此据仇注引,今本《杜臆》文字有异)黄生说:“杜诗强半言愁,其言喜者仅寄弟数作及此作而已(2)。言愁者真使人对之欲哭,言喜者真使人读之欲笑,盖能以其性情达之纸墨,而后人之性情类,为之感动故也。学杜者不此之求,而区区讨论其格调,剽拟其字句,以是为杜,抑末矣!”各有所见,俱佳。
还乡梦终于成了场白日梦。春天,老杜回不了洛阳,也回不了成都,仍在梓州淹留。他到处登临游览,偶尔参加些饮宴、送迎等社交活动,写了些记事、抒怀的诗篇,从中可窥诗人行止、心境之一斑。
《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当作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喜讯后不久。其一说:
“行路难如此,登楼望欲迷。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羁栖。江水流城郭,春风入鼓鼙。双双新燕子,依旧已衔泥。”新燕又来城楼筑巢定居了,而旅人仍浪迹羁栖,徒伤老大。风送鼓鼙,时犹未靖;水流城郭,江路邅回。王粲《登楼赋》说:“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谁知四望凄迷,反惹出闲愁如许!仇兆鳌说:“杜律首句,有语似承上,却是突起者。如‘杖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故人亦流落,高义动乾坤’‘行路难如此,登楼望欲迷’,既飘忽,又陡健,此皆化境语也。”这诗中的“迹有但羁栖”即《远游》中“迷方著处家”之意。梓州客居情况不详,但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种药扶衰病”(亦《远游》中句,该诗作于梓州)如故。想到老杜流落他乡,贫病交加,靠采药种药供自己和家人保健,或换钱补贴家用,这也是够惨的了。其二说:
“天畔登楼眼,随春入故园。战场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李白《寄东鲁二稚子》:“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又《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质言之,这都不过是说想念之极,不胜神往。如果换种说法,说我的心给风刮到我所思念的人的身边,或我所向往的地方,那岂不令人目瞪口呆,惊讶他构思的奇特和表现力的强烈吗?懂得了李白那两首诗中的那颗“心”,就懂得这诗中老杜的这双“眼”了。“心之所至,目亦随之,故登楼一望,而天畔之眼,遥入故园。因思战场始定,而故园之柳更存否也?”(王嗣奭语)真是诗人打发他的双眼遥入故园吊刚刚平定的今战场去了。转思北归暂恐未能,便又作东游之想。吴越胜事本繁,何况时平年少,回想更增向往。蜀中交游实冷,加之世乱身衰,现状能不厌烦?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老杜的厌蜀思吴完全可以理解,值得同情。老杜入蜀以来,常想重游吴越。去岁来梓州,一直在筹划此事,今见时机成熟,去志更坚了。“长啸下荆门”,感情色彩强烈,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恶气!
《春日戏题恼郝使君兄》,是首颇有资料价值的作品:
“使君意气凌青霄,忆昨欢娱常见招。细马时鸣金??,佳人屡出董娇饶。东流江水西飞燕,可惜春光不相见。愿携王赵两红颜,再骋肌肤如素练。通泉百里近梓州,请公一来开我愁。舞处重看花满面,樽前还有锦缠头。”仇兆鳌于《答杨梓州》题下案:“据前有李梓州,后有章梓州,此又有杨梓州,一岁而有三梓州,何更代之速耶!”通泉是梓州属县,不当设刺史;此“郝使君”亦不当为梓州刺史(若然,依前诗例当称郝梓州;且一年四梓州,似无此理),或是辞官或休沐还乡居于通泉的他州刺史。据诗中所述,此人当是当地富豪,犹如《从事行》中的严二别驾一样。去冬老杜在通泉时,常被郝某邀去参加宴会;席间,郝出其王、赵二姬以歌舞侑酒。今年春暖花开,老杜在梓州偶然忆及当时欢娱情景,因戏题此诗,望郝携妓来梓州为他开愁解闷。仇兆鳌说:“百里携妓,势所不能,亦空想花容而已。故曰‘戏’、曰‘恼’也。”“细马时鸣金??,佳人屡出董娇饶”“再骋肌肤如素练”“舞处重看花满面”……得美而艳,见老杜生活和心理未能免俗的一面。同时所作《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也是这样一类作品。其一说:“上客回空骑,佳人满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玉袖凌风并,金壶隐浪偏。竟将明媚色,偷眼艳阳天。”其二说:“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床。翠眉萦度曲,云鬓俨成行。立马千山暮,回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仇兆鳌说:“唐人《五日观妓》诗:‘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谁道五丝能续命,却令今日死君家。’此纵情徇欲,少年无赖之谈,岂可列于风雅中乎?杜公《陪李梓州泛江》咏诸舫女乐云:‘翠眉萦度曲,云鬓俨成行。’结语则云:‘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姚通泉携酒泛江》咏彩舟美人云:‘笛声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结语则云:‘人生欢会岂有极,无使霜露沾人衣。’观此二诗,能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有节,可以见公之所养矣。”老杜的这一类诗,至多能见出旧日官僚生活的奢华腐化,和老杜当时交游之一斑,不可曲为辩解,任意抬高。
这年春天,不知怎的,经梓州或回成都、或归朝、或下峡的亲友也特别多。可能他已动了去蜀之念而未及成行,因此每遇离筵,倍觉伤神:“二月频送客,东津(3)江欲平。烟花山际重,舟楫浪前轻。泪逐劝杯下,愁连吹笛生。离筵不隔日,那得易为情。”(《泛江送客》)
梓州治郪县。一天,他在郪城西原饯送李判官、武判官去成都,作《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说:
“凭高送所亲,久坐惜芳辰。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野花随处发,官柳著行新。天际伤愁别,离筵何太频!”客中送客,情何以堪?这诗写得倒也真挚,只是太感伤了。当然这还要看对什么人,他的《惠义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得峰字》就不是这样:“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峰。阑干上处远,结构坐来重。骑马行春径,衣冠起暮钟。云门青寂寂,此别惜相从。”前老杜作《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惠义寺所送当是那位王少尹。王或因公来梓州,今事毕复返成都。这是官场应酬、即席分韵赋诗之作,无甚可观,末句微露相偕回成都之意。兜率寺在郪县城南二里,详后。
最易触动老杜心弦的,是送人还京。他的《泛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说:
“迟日深江水,轻舟送别筵。帝乡愁绪外,春色泪痕边。见酒须相忆,将诗莫浪传。若逢岑与范,为报各衰年。”黄鹤以为玄、肃二宗是年三月葬,故有“帝乡愁绪”“春色泪痕”之句。理解过于狭窄;老杜此时必然感慨万千,非止于哀悼故君。仇兆鳌说:“公时多伤时语,故嘱其莫浪传以取忌。”甚是。范季明不详。岑参,上元二年在虢州。宝应元年春,改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关西节度判官。十月,天下兵马元帅雍王适会诸道节度使于陕州,进讨史朝义,以岑为掌书记。广德元年,正月入京,在御史台供职。秋,任祠部员外郎(详《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这年春,太子中允仍为岑的本职,故称“中允”。“为报各衰年”,是说请魏将自己年老体弱的情况逐个地告诉岑与范。老杜任左拾遗时,曾与人联名保荐岑参为右补阙。如今岑参在朝地位已不低,老杜固然会为老友的际遇高兴,但相形之下,更显出自己的蹇剥,这就无怪他要感慨系之了。这种天涯迟暮、伤春惜别的情怀,也同样强烈地表露在《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得山字》诗中:“追饯同舟日,伤春一水间。飘零为客久,衰老羡君还。花杂重重树,云轻处处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鬓毛斑。”另一首《送路六侍御入朝》,因为送的是童年老友,情真意挚,写得就更好:“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不分桃花红似锦,生憎柳絮白于绵。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不分”,不料。春意愈浓就愈能触动离人愁思,甚至连酒也排遣不了,于是泄愤于桃花柳絮了。前两年春天,他写诗表示怕春怪春恼花(《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江上被花恼不彻”“行步欹危实怕春”,《绝句漫兴九首》“无赖春色到江亭”“便教莺语太丁宁”),也是这意思。李子德说:“一气滚注,只如说话,而浑成不可及。”此等诗,只须稍加吟咏,自知其妙。又有《送何侍御归朝》,题下原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这只是一般应酬,诗也平常:“舟楫诸侯饯,车舆使者归。山花相映发,水鸟自孤飞。春日垂霜鬓,天隅把绣衣。故人从此去,寥落寸心违。”仇兆鳌以为山花映发,起下绣衣故人,见侍御归朝之乐;水鸟孤飞,起下霜鬓寸心,见异方作客之穷:兴中有比,杜诗善用此法。此解颇佳,见作者针线之密,或有助于初学揣摩技法。
他的《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写得较有意思:“无数涪江筏(4),鸣桡总发时。别离终不久,宗族忍相遗?白狗黄牛峡,朝云暮雨祠。所过凭问讯,到日自题诗。”《新唐书·百官志》:“都水监,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掌川泽、津梁、渠堰、陂池之政,总河渠、诸津监署。”仇兆鳌说:“崔为都水使,与公为甥舅,故称曰翁。下峡,将归洛阳也。旧注谓归长安,反纡途矣。公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此可证也。”若首联确如仇注所解,谓“筏多桡响,从行者众”,则崔系因公顺流而下巡视沿途水利,因此就不存在“归长安反纡途”的问题。当然,他也很可能由长江转汉水至襄阳起旱归洛阳,但总得回长安销差。不可拘看。《十道志》载白狗峡在归州(今湖北秭归),两崖如削,白石隐起,其状如狗;黄牛峡在夷陵州(今湖北宜昌市),石色如人牵牛之状,人黑牛黄。宋玉《高唐赋序》:“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古时或有巫山神女祠。前引《送何侍御归朝》首联“舟楫诸侯饯,车舆使者归”,写刺史泛舟设宴饯送侍御归朝场面,很有气派。这诗首联写都水使率众“鸣桡总发时”情景,就显得更加神气了。颔联上句得到下句的补充,意思才完全,这仍然是流水对:咱们离别不久终会再见的,因为我有亲族在京,不忍遗弃,我很快也要下峡还乡了。《杜臆》:“五、六,纪一路所经。所过有相知,凭翁问讯,云‘到日自题诗’以赠也。”顾注:“将来欲凭此以问安信,何不按日题诗留存手迹乎?”卢注:“张籍《送远曲》:‘愿君到处自题名,他日知君从此去。’即末二句意。”仇兆鳌以为后二说太曲,还从《杜臆》为当。顾串讲,卢印证,实是一说。此说确太曲,若照此理解,语句则不如张籍二句流畅,有损诗意。前说虽顺,惜与本有内在联系的颈联脱节,而另设所谓“相知”作为“问讯”对象,似亦非作者本意。私意《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尾联连用“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四地名以见归心之急,而本诗颈联“白狗黄牛峡,朝云暮雨祠”,指的其实只是白狗峡、黄牛峡、巫山神女祠三处,在诗中所起作用也有所不同。老杜入蜀以来,尤其到梓州以后,常思下峡,而沿途胜迹他所心向往之、渴望在不久的将来顺道一游的,当是这样一些地方。(“一自《高唐赋》成后”,巫山神女峰于我国古代文士印象之深就不须说了。盛弘之《荆州记》载古歌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李白《上三峡》也说:“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黄牛峡也很引人注意。白狗峡与黄牛峡相对成趣,故及之。)于是,他就托下峡的崔翁经过这些胜迹时先代问讯,等他不久到来时再一一题诗。或问:岂得向白狗、黄牛、神女问讯?谁说不能!老杜不是在《重过何氏五首》其一中就曾“问讯东桥竹”(详第七章第一节),在《送韦郎司直归成都》中也托韦郎“为问南溪竹”么?既可问竹,当然更可问山川灵异了。这不过是修辞中常用的拟人手法。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当时老杜去蜀之计已定,一旦准备就绪,即可成行了。神往之情一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但一强烈,一隽永,风味因情境不同而小有差异。颈联是宽对,又各是句中对;妙手偶得,别饶风致,不觉纤巧。
此外还有《送元二适江左》,但不知是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的那位元二否。
相关阅读
文章标题:狂喜过后-杜甫“蛟龙无定窟”
链接地址:http://www.shootiniron.com/jianjie/852.html
上一篇:一波又起-杜甫“蛟龙无定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