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伤雄才”-杜甫转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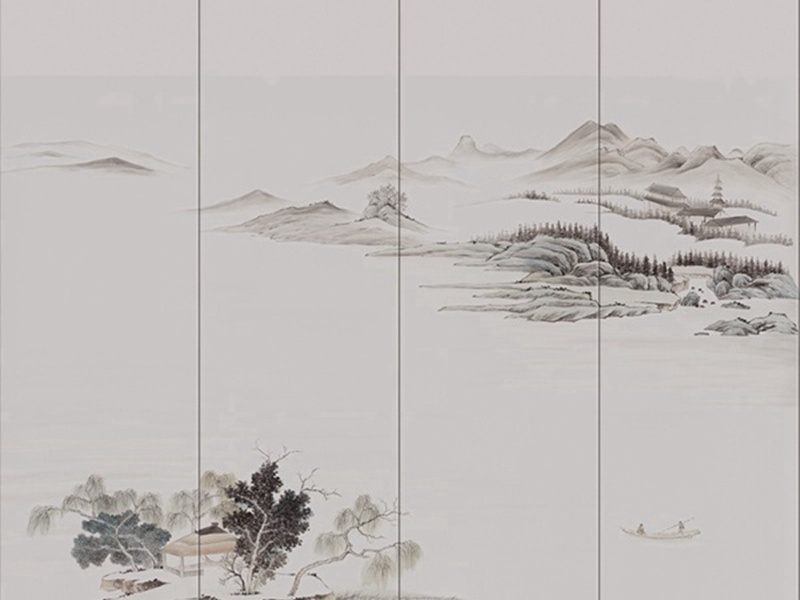
高适和诗不存。不知是高适回信说暂时不宜回成都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这年冬天老杜却往陈子昂的故乡射洪(旧治在今四川射洪县金华镇)游览凭吊去了。射洪在梓州东六十里。境内有金华山。金华山在县城之北二里,县城又在涪水之西一百步。老杜初来射洪时在城边野望,作《野望》说:
“金华山北涪水西,仲冬风日始凄凄。山连越隽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独鹤不知何事舞?饥乌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绿,极目伤神谁为携?”唐隽州越隽郡治所在今四川越西县。常璩《蜀志》载:秦置蜀郡,汉高祖置广汉郡,武帝又分置犍为郡,后人谓之三蜀。十一月风日惨淡的一天,我站在涪水之西眺望,北边就是金华山。那金华山,山连着山,蟠曲在三蜀境内。这涪水,流到巴县、渝州(州治在巴县,即今四川重庆市),再下又有武陵五溪(雄溪、樠溪、酉溪、?溪、辰溪,在今湖南西部)流入。独鹤多像个孤单的客子,不知它为什么却在跳舞?饥乌聒噪,似乎想向人乞食。射洪的春酒,到天寒时仍然碧绿。我触目伤神,可又有谁携酒来同我遣闷销愁?——据此可知他来射洪在这年十一月(“仲冬”),当时他的心情是不好的。
大概在城边眺望写作前诗后不久,老杜登上金华山,参观了山上的金华观,找到了陈子昂的学堂的遗迹,很有感触,作《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说:
“涪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系舟接绝壑,杖策穷萦回。四顾俯层巅,淡然川谷开。雪岭日光色,霜鸿有余哀。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陈子昂读书堂,在射洪县北金华山。大历中,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为立旌德碑于读书堂(27),堂在玉京观(本名金华观,宋改名玉京)后。金华山上拂云霄,下瞰涪江。相传东晋陈勋学道山中,白日飞升。梁天监中建观。有老君像,唐明皇所铸(见《舆地纪胜》《新修潼川府志》等)。陈子昂有《春日登金华观》云:“白玉仙台古,丹丘别望遥。山川乱云石,楼榭入烟霄。鹤舞千年树,虹飞百尺桥。还疑赤松子,天路坐相邀。”可见当时此间建筑与景物的一斑。彭庆生《陈子昂诗注》:“本集卷七《晖上人房饯齐少府使入京府序》云:‘永淳二年(六八三)四月孟夏云云。朝廷子入,期富贵于崇朝;林岭吾栖,学神仙而未毕。’可证子昂进士及第之后,曾居家学仙,诗当作于此时。”据诗中所述,老杜这天来游时天气很好。他在船上远远地望见涪水西岸众山之中就数那紫色的金华山最高。从冬日蔚蓝色的天空中垂下的阳光,拥抱着山上道观的琼楼玉宇。把船靠在绝壑下面,就拄着拐棍儿在盘旋往复的山路上攀登。登上山顶四下观望,那川流那山谷隐隐约约地展现在眼前。西边那雪岭在阳光照射下泛出苍白的死色(28),霜天传来了鸿雁的哀鸣。道观里跪着烧香的信女犹如玉女,访道的善男来了仿佛是雾里降临的仙人。(29)陈公读书堂柱仄苔青,悲风似乎为他而起,他情怀激烈,为雄才的含冤殒命而深深伤悼。
老杜前在绵州,遇李使君去梓州上任,曾作诗嘱李来日行部至射洪为他洒泪凭吊陈子昂:“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如今他亲来射洪,自然要寻陈子昂的遗迹,深致悼念之意了。接着他又参观了陈的故居,作《陈拾遗故宅》说:
“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扬荒山日,惨澹故园烟。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彦昭超玉价,郭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银钩连。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子昂故宅在射洪县北里许的东武山下。(30)陈子昂《梓州射洪县武东山故居士陈君碑》:“君讳嗣(子昂叔祖),……其先陈国人也。汉末沦丧,八代祖(陈)祇(子昂十世祖),自汝南仕蜀为尚书令。其后蜀为晋所灭,子孙避晋不仕,居涪南武东山。与唐、胡、白、赵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县,而四姓宗之,世为郡长。”又《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公讳元敬(子昂父),……五世祖太乐(子昂六世祖),梁大同中为新城郡司马。生高祖方庆(子昂五世祖)。方庆好道,得《墨子》《五行秘书》《白虎七变法》,遂隐于郡武东山。……青龙癸未,唐历云微。公(子昂父元敬)乃山(当是武东山)栖绝谷,放息人事。”据此可知:(一)自晋初以来,陈氏即聚族居于武东山(后世方志作东武山),世代为当地豪族。(二)子昂五世祖陈方庆与其父陈元敬都隐居于武东山学道。子昂的山栖学仙,“林岭吾栖,学神仙而未毕”,显然也受到家族的影响。这诗先记子昂故居,大屋修椽,现尚完整如昔,以及荒山寒日、故里风烟景象。次赞其位下才高,上薄风骚,下与扬雄、司马相如接踵,名垂千古。卢藏用《陈氏别传》:“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扬、马都是蜀人,故用以相比。复志其交游遗迹。诗人因见壁上题字,知赵彦昭与郭元振曾来此宅,与之同游。
赵彦昭,字奂然,甘州张掖(今甘肃张掖)人。少豪迈,风骨秀爽。及进士第,调为南部尉。与郭元振、薛稷、萧至忠相友善。中宗景龙中,累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睿宗立,出为宋州刺史。入为吏部侍郎。萧至忠、薛稷等依附太平公主反对玄宗。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谋反,玄宗与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等定计先下手。执萧至忠等于朝堂斩之。薛稷赐死于万年狱。太平公主赐死于家。萧至忠等被诛后,郭元振、张说等称赵彦昭曾参预平乱密谋,以功迁刑部尚书,封耿国公。赵彦昭本以权幸得进。中宗时有巫赵五娘,以左道出入宫禁。赵彦昭以姑事之,曾着妇人衣,乘车与其妻前往拜谒,以表侄子之情。他得为宰相,全仗赵五娘之力。于是殿中侍御史郭震(此人与郭元振同名)弹劾他的旧恶。时姚崇执政,恶其为人,贬为江州别驾,卒。《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十一首,多应制之作,无甚可观。郭震,字元振,以字显。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东南)人。少有大志。十六岁,与薛稷、赵彦昭同为太学生,家中刚送来四十万钱,恰好有个着丧服的人叩门,自言:“五世未葬,愿假以治丧。”郭元振毫不吝惜,竟将钱全部给了他,也不问他的姓名,薛稷等都很惊叹。十八岁举进士,为通泉尉。任侠使气,不拘小节,曾盗铸并掠卖部中口千余,以饷遗宾客,百姓厌苦。武后得知,把他召去诘问,一同他交谈,便感到很惊奇,索所为文章,上《宝剑篇》,武后看了很夸奖,即授右武卫铠曹参军。大足元年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筑要垒,开屯田,在职五年,军粮充足。神龙中迁安西大都护。睿宗立,召为太仆卿。景云二年,进同中书门下三品,迁吏部尚书。玄宗诛太平公主,郭元振立大功,进封代国公。玄宗讲武骊山,他坐军容不整流新州。旋起为饶州司马,病死途中。《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十三首。《宝剑篇》《塞上》均有风骨。小诗学南朝乐府民歌,如:《春江曲》“江水春沉沉,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清丽可诵;《惜花》“艳拂衣襟蕊拂杯,绕枝闲共蝶徘徊。春风满目还惆怅,半欲离披半未开”,亦别饶情趣。唐南部县即今四川南部。唐通泉县今并入射洪。赵、郭与陈子昂同游,并登府题壁,当在二人分别为此二县县尉时。《碑目》载陈子昂故宅有赵、郭题壁。这题壁据老杜的描绘“洒翰银钩连”,知是草书。末叹盛事已往,堂宇终将湮灭,但诗留忠义,自足千古。王嗣奭说:“会止一时,堂不千年,独《感遇》之遗编尚存,此立言而垂不朽者也。称文章而归之‘忠义’,才是真本领,亦公自道。‘位下曷足伤’二语,亦自道。‘终古立忠义’,观集中所上书疏及本传可见,非谓《感遇》诗。若《感遇》诗当世推为文宗,人皆知之。而公复推于忠义,特阐其幽,亦见所重自有在也。”
陈子昂(六六一—七〇二),字伯玉,出身豪富之家,任侠使气,到十七八岁尚不知书。曾随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谢断门客,专心读书,数年之间,学问精进。武后光宅元年(六八四),二十四岁,游东都,举进士对策高第,擢麟台正字。垂拱二年(六八六),从乔知之北征金徽州都督仆固始。永昌元年(六八九),补右卫胄曹参军。天授元年(六九〇),九月,武后改国号为周。他上表进《大周受命颂》四章并序表示拥护。次年春,以继母丧解官返里。长寿二年(六九三)回东都,擢右拾遗。延载元年(六九四)坐逆党入狱。天册万岁元年(六九五),出狱,官复原职。九月,建安王武攸宜讨契丹,子昂以本官参谋。神功元年(六九七),在军幕。武攸宜轻易无将略,子昂谏以严立法制,以长攻短,不纳,降为军曹,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泫然涕流,作《登幽州台歌》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七月凯旋,仍守原官。圣历元年(六九八),以父老上表解官归侍,诏听带官而归。次年七月七日,其父陈元敬卒。长安二年(七〇二),卧病家中。本县令段简闻其家富有,乃附会法律,欲害子昂,家人纳钱二十万,段简嫌少,系狱而卒(以上事迹均据罗庸《陈子昂年谱》)。中唐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曾论及乔知之与陈子昂的死:“乔死于谗,陈死于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时之情,致力克害。一则夺其妓妾以加憾;一则疑其摈排以为累,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于非命。”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尝怪陈射洪以拾遗归里,何至为县令所杀。后读沈亚之《上郑使君书》,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录以备考。
葛晓音《关于陈子昂的死因》(载《学术月刊》一九八三年二月号)说:“我认为陈子昂之死的原因更可能是段简根据陈子昂所写府君墓志铭一文,‘附会文法’,以子昂诋毁武后、‘指斥乘舆’、‘无人臣之礼’为名,勒逼财物,陷其下狱,致使本来就哀毁羸疾的陈子昂不堪折磨而死。”论证颇详,所见近实,较他说可信。陈子昂是有卓识有胆略的政治家,也是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旗手。作为政治家,他敢于通过谏疏陈述并坚持自己进步的政见:一、关注民瘼,改革吏治;二、揭露酷吏,反对淫刑;三、重视边防,反对黩武;四、主张任用贤能,用人不疑。作为文学家,他在《修竹篇序》中大声疾呼,反对齐梁以来的华靡诗风,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革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而他多年创作的《感遇》三十八首及其他名篇,或讽刺现实、批判时政,或感伤身世、抒发豪情,无不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他的理论和实践,犹如动地狂飙,尽扫弥漫唐初诗坛的浮靡余风,为其后盛唐诗歌的发展清除了道路,功绩不小,影响深远。韩愈的《荐士》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后来相继者,亦各臻阃奥。”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其八说:“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以诗论诗难免夸大,而其基本评价却不为大谬。大体说来,自古至今,论者对陈子昂在唐诗发展上的开山地位多无异议。至于谈到他对待武后的态度问题,前人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分成肯定和否定的两派。最早宋朝的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显斥陈子昂“无风节”。此派看法,愈演愈烈,到了清代,王士祯说:“(子昂)《上大周受命颂表》一篇、《大周受命颂》四章,其辞谄诞不经。又有《请追上太原王帝号表》,太原王者,士彟也,此与扬雄《剧秦美新》无异,殆又过之,其下笔时不知世有节义廉耻事矣,子昂真无忌惮之小人哉!诗虽美,吾不欲观之矣。”(《带经堂诗话》)潘德舆甚至将陈子昂连同阮籍一并加以斥责,且对老杜《陈拾遗故宅》“有才继骚雅”“终古立忠义”云云表示不满:“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小缪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诗不得恕之。……以人而论,则籍之党司马昭而作劝晋王笺,子昂谄武曌而上书请立武氏九庙,皆小人也。……杜公尊子昂诗,至以‘骚雅’‘忠义’目之,子乌得异议?曰:子昂之忠义,忠义于武氏者也,其为唐之小人无疑也。”(《养一斋诗话》)那么,肯定陈子昂人品的一派,尤其是老杜给予他“终古立忠义”的崇高评价,是不是就错了呢?对待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这样回答:武则天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指责陈子昂忠于武家而不忠于李家,这看法本身就很封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是可笑的。这答复当然是对的。可是武后执政时确有不少希宠干禄的小人,从陈子昂积极拥护武后建周称帝的表现看,也并不是毫无可非议之处,所以对于陈子昂的人品,仍须做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这一问题,评论得最早也最具体的是《新唐书·陈子昂传赞》:“子昂说武后兴明堂太学,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窃威柄,诛大臣、宗室;胁逼长君而夺之权。子昂乃以王者之术勉之,卒为妇人讪侮不用,可谓荐圭璧于房闼,以脂泽污漫之也。瞽者不见泰山,聋者不闻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聋瞽欤?”认为武后很坏,未免带有偏见。认为陈子昂“以王者之术勉之,卒为妇人讪侮不用”,政治上真是又聋又瞎,教人可怪可笑,这指责虽然极其严厉,却并未怀疑他的人品,把他看成无耻小人。比较起来,王夫之对陈子昂人品和政治表现的评价最全面也最中肯:“陈子昂以诗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选也,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颉颃姚崇,以为大臣可矣!其论开间道击吐蕃,既经国之远猷;且当武氏戕杀诸王、凶威方烈之日,请抚慰宗室,各使自安,撄其虓怒而不畏;抑陈酷吏滥杀之恶,求为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而贼臣凶党,弗能加害,固有以服其心而夺其魄者,岂冒昧无择而以身试虎吻哉?故曰:以为大臣任社稷而可也。载观武氏之世,人不保其首领宗族者,蔑不岌岌也。而子昂与苏安恒、朱敬则、韦安石,皆犯群凶,持正论而不挠;李昭德、魏元忠、李日知,虽贬窜而终不与傅游艺、王庆之、侯思止、来俊臣等同受显戮。由是言之,则武氏虽怀滔天之恶,抑何尝不可秉正以抑其妄哉?而高宗方没、中宗初立之际,举国之臣,缩项容头,以乐推武氏,废夺其君,无异议者。向令有子昂等林立于廷,裴炎、傅游艺其能仇匿以移九鼎乎?”(《读通鉴论》)所举陈子昂的种种政治表现都是事实,王夫之从中看出:一、陈子昂不仅有远见卓识,而且有勇有谋,善于在险恶的政治情况下进行斗争,充分显示出大政治家的才具和品质;二、要是朝廷上像陈子昂这样的人多了,即使武后不好,还是可以“秉正以抑其妄”的。私意以为,仅就对陈子昂而论,这两点看法基本是正确的。
前两年,我读《陈子昂集》,发现《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如下的一些记述,对研究陈子昂的思想和政治倾向很有帮助:“公讳元敬,……二十二,乡贡明经擢第,拜文林郎。属忧艰不仕,潜道育德,穆其清风,邦人驯致,如众鸟之从凤也。时有决讼,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杰,望风景附,朝廷闻名。或以君为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让以德也。州将县长,时或陈议。青龙癸未,唐历云微。公乃山栖绝谷,放息人事,饵云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图天象,无所不达。尝宴坐,谓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观大运,贤圣生有萌芽,时发乃茂,不可以智力图也。气同万里,而遇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无一焉。呜呼,昔尧与舜合,舜与禹合,天下得之四百余年。汤与伊尹合,天下归之五百年。文王与太公合,天下顺之四百年。幽历板荡,天纪乱也。贤圣不相逢,老聃、仲尼,沦溺溷世,不能自昌。故有国者享年不永,弥四百余年,战国如麋,至于赤龙。赤龙之兴四百年,天纪复乱,夷胡奔突,贤圣沦亡,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将周复乎?於戏,吾老矣,汝其志之。’太岁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隐化于私馆。……是岁十月己酉,遂开拭旧茔,奉宁神于此山石佛谷之中冈也,铭曰……”陈子昂父陈元敬卒于圣历二年己亥(六九九),时年七十四岁,则“二十二,乡贡明经擢第”当在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随即拜文林郎,后因丁忧不仕。但真正决心归隐却在“青龙癸未”弘道元年(六八三)高宗逝世、“唐历云微”之际。由此可见陈元敬是坚决反对武后擅权的。既然陈元敬反对武后的政治态度是这样地坚决,后来又对陈子昂讲过当时正值天纪复乱、贤圣不相逢、不可以智力图之的大道理,而且要陈子昂记在心里,那么,当圣历二年十月作此墓志文之时,亦即陈子昂积极从政多年而终告失败之后,他竟不惮时议,提起这段往事,并在铭中给他父亲以极高的评价,甚至以孔子、商山四皓与之相比:“贤者避地,邈其往兮。凤兮凤兮,谁能象兮!呜呼我君,怀宝不试,孰知其深广兮!悠悠白云,自怡养兮。大运不齐,贤圣罔象兮。南山四君,不遭汉天子,固亦商丘之遗壤兮。”肯定父亲的见机识时,就是承认自己不顾天运欲以智力图之的无知和劳而无功。这岂不表明陈子昂开初的竭诚“以王者之术勉”武后,确乎如王夫之所说,是有意识地在“秉正以抑其妄”么?这样看来,讥笑“子昂之于言,其聋瞽欤!”,骂他是“真无忌惮之小人”,都未免太冤枉他;而老杜说他“终古立忠义”,倒是最知其用心良苦的了。或者说,《陈子昂集》有《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对杜审言的文才推崇备至:“杜司户炳灵翰林,研几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独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老杜的《壮游》“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显系受序中“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的影响,可见他对这序很熟习,对陈子昂同他祖父的关系很清楚。老杜的封建感情颇强烈,因此他对其世交前辈陈子昂的评价难免过当,不足为凭。这话不无道理,比如他祖父杜审言的友人宋之问,倾心媚附武后的宠幸张易之,“至为易之奉溺器”,“天下丑其行”(《新唐书·宋之问传》),但他在《过宋员外之问旧庄》诗中,还对宋之问,表示通家晚辈深深的凭吊、感叹之意。虽然如此,每当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时,他还是很谨慎的。第一章第二节中曾经谈到,他祖父杜审言交接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人品比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稍微好一些,也不算很高尚。老杜很敬佩他祖父的文学成就,常以他家有他祖父所开创的诗歌传统而自豪。可是,当他认真评论历史时,却直言不讳地指出:“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八哀诗·赠秘书监汇夏李公邕》)这“宠嬖”即指二张之流。他对他祖父的政治表现,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微辞,心里还是有看法的,起码会感到与这些“宠嬖”有牵连未免窝囊。又说开元二十九年老杜漫游齐鲁之后归洛阳,筑陆浑庄于首阳山下。这年寒食,他为文祭远祖杜预而不祭祖父杜审言,可见远祖和祖父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对自己的祖父尚且如此,要是他心里真认为陈子昂在“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时德行有亏,今来故宅游览,即使要作诗,他尽可像《过宋员外之问旧庄》那样,深致通家晚辈凭吊、感叹之意即可,又何必发违心之论呢?要知道,老杜是忠于李唐王室而明确表示不满武后的。站在他的立场,哪会轻易以“忠义”许人?要是我前面所作关于陈子昂人品和政治表现的探索差可成立,那么老杜可算是最早的最理解陈子昂的了。陈子昂曾为右卫胄曹参军、右拾遗,老杜曾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左拾遗,这偶然的近似,可资谈助。
在射洪他还写作了《谒文公上方》和《奉赠射洪李四丈》二诗。前者首记上方景象,次赞文公道行,末叙来谒欲皈依佛法之意。此诗不甚佳,苏轼却称道其中“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原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及其他诗句,以为据此“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见《东坡题跋》)。王嗣奭说:“王侯与蚁同尽,不过袭《庄》《列》语;‘愿闻第一义’,亦禅门常谈。东坡以此四句卜得其道,此窥公之浅者。余读公诗,见道语不一而足,而公亦不自知也,非以学佛得之。平生饥饿穷愁,无所不有,天若有意煅炼之;而动心忍性,天机自露,如铁以百炼而成钢,所存者铁之筋也,千年不磨矣。”强调老杜对哲理的领悟主要得力于人生历练而不是学佛,这是很有见地的。《奉赠射洪李四丈》说:
“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人生意气豁,不在相逢早。南京乱初定,所向色枯槁。游子无根株,茅斋付秋草。东征下月峡,挂席穷海岛。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苍茫风尘际,蹭蹬骐?老。志士怀感伤,心胸已倾倒。”诗题下自注李四字“明甫”。这诗首四句如谣谚,叙二人相见虽晚却甚相得。次叹成都经乱,草堂不可复居;欲出三峡,又苦无川资。末以骐?自喻,志士谓李;一蹭蹬,一感伤,遭遇相同,意气故相投。
这两首诗,略见老杜在射洪的行踪、交往和思想情况。老杜前在梓州作《悲秋》说“始欲投三峡”,今又说“东征下月峡”,可见他当时携眷出峡的念头很强烈,只因无钱未能成行。
相关阅读
文章标题:“激烈伤雄才”-杜甫转蓬
链接地址:http://www.shootiniron.com/jianjie/848.html
上一篇:旅梓游踪-杜甫转蓬
下一篇:“此行叠壮观”-杜甫转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