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濡以沫的日子里-杜甫的惊变与陷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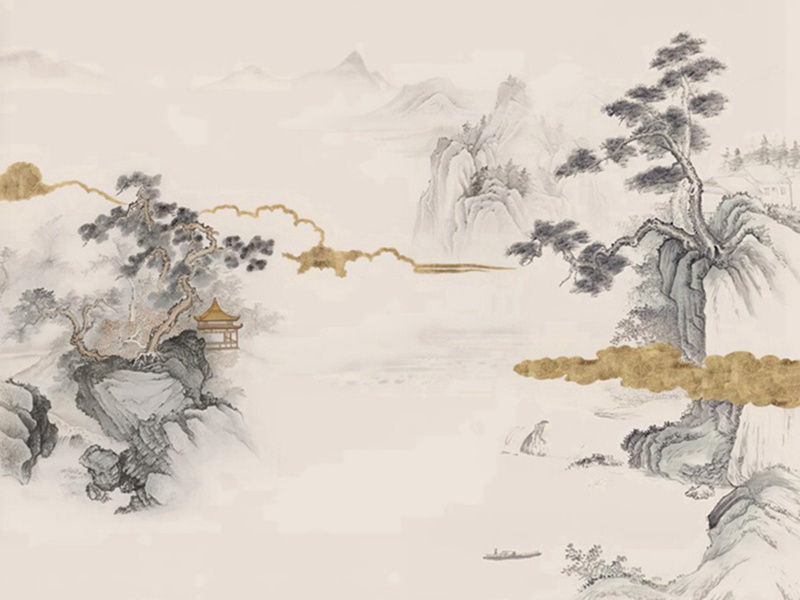
在这个倒霉的春天里,老杜除了偶尔偷偷地溜到曲江这样的昔日游乐地去伤今忆旧,抒发家国身世之悲,也常与长安城中几位相知的僧俗友人来往,或趁食,或谈心,总之是相濡以沫,聊以度日。《长安志》载大云经寺在京城朱雀街南,怀远坊东南隅;本名光明寺,武后初幸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名,并令天下诸州置大云经寺。当时长安大云寺住持僧赞公对老杜很友善,曾留他在寺里住宿,供饮食,送履巾,照顾得真是无微不至。老杜深为感动,就写作了《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一说:
“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时。洞门尽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开复闭,撞钟斋及兹。醍醐长发性,饮食过扶衰。把臂有多日,开怀无愧辞。黄鹂度结构,紫鸽下罘罳。愚意会所适,花边行自迟。汤休起我病,微笑索题诗。”此初过寺中而记其胜概。江总《大庄严守碑》:“影彻琉璃之道,光遍水精之域。”“心在”句出此,妙处不仅在用典恰当,更在借“水精域”的联想,显示他离乱世红尘而乍一到此净界所生超脱而圣洁的心理状态。“衣沾”句有季节感和生活实感。杨伦以为“到扉”句是“不欲俗人过从也”。若理解为描状了战乱中寺院僧人惊惶不安、唯恐坏人闯入的神态,亦复大佳。僧家设“斋”,每“撞钟”而会食。“醍醐”是酥酪上凝聚的油。《本草纲目·兽一》“醍醐”引寇宗奭的话说:“作酪时,上一重凝者为酥,酥上如油者为醍醐,熬之即出,不可多得,极甘美。”佛教用以比喻一乘教义。
如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五:“譬如因乳得酪,因酪得酥,因酥得醍醐。真解脱中都无是因,无是因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发性”出《止观辅行》:“见是慧性,发必依观;禅是定性,发必依止。”“过”,过甚,过分。“扶衰”出《汉书·食货志》:“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醍醐”句夹在“撞钟”句与“饮食”句之间,前后俱述设斋会食情事,不能径采王洙注,以为这只是称美赞公,说听他说法,如醍醐灌顶;而应该转个弯,从席间酥酪、醍醐之类精美的斋食而引出这一不无幽默意味的想法:原来就是从这种食品中长久地生发出佛性来的啊!怀素《食鱼帖》说:“老僧在长沙食鱼,乃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咲(笑),深为不便,故久病不能多书,实疏还报,诸君欲兴善之会,当得扶羸也。九日怀素藏真白。”怀素作草书是很费气力的:“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李白《草书歌行》)他来到长安,不便吃肉,写字没劲儿,欠了不少“字”账没法还,就说谁若是要他写字,就得先给他滋补滋补。据说长安大户人家争着请他写字,先预备一面白粉墙,等他酒醉饭饱之后,便振笔疾书,一挥而就。评者谓张旭为颠,怀素为狂。他私下问人要肉吃,真是够狂的了,但到底怕人笑话,不敢公开吃肉。可见长安不像长沙,是不允许和尚吃荤,寺院中待客也无疑是用素食的啊。帖中的“扶羸”就是诗中“扶衰”的意思,是说补养一下虚弱的身子。太平年月,作为和尚的怀素,没肉吃尚且叫苦连天,说要增加点营养。敌离时世,老杜在寺院里叨扰了几顿“淡出鸟来”的素食,竟感激不尽,说什么“饮食过扶衰(饮食中的营养已大大超过了滋补身子的需要)”,他当时生计的窘迫,可想而知。南朝刘宋时沙门惠休善属文,本姓汤,此“汤休”借喻赞公。“起我病”承“扶衰”“把臂”意。末二句谓:来此多日,承赞公盛情款待,亲切交谈,使我病痛消除,心身舒泰;赞公见我如此,便欣然向我索取诗句来了。
《杜臆》说:“公诗人,意适行迟,诗兴动矣。赞会其意,故‘微笑索题’,景况殊妙。‘起我病’,谓有好诗之癖。”如此解说亦通,可参看。浦起龙说:“‘斋及兹’,适然初款。‘醍醐’‘饮食’,特设矣,正述‘多日’‘开怀’时。仇即指及兹之斋,非是。但‘开怀’自有心心相契处。吴论云‘开怀享食’,陋甚。‘意会’‘行迟’,赞公同步,与前‘徐步’‘幽期’各别。结亦有神,一往幽微,尽入拈花一笑也。钟惺曰:‘诗有一片幽润灵妙之气,浮动笔端。’”剖析细致,引钟惺语亦佳。“黄鹂”是寺院和平静穆景象,写得有气氛。
其二:“细软青丝履,光明白㲲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顾转无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远德过人。雨泻暮檐竹,风吹春井芹。天阴对图画,最觉润龙鳞。”前半截谢赠履巾,言此二物“宜供养老宿,今取赠吾身,自顾殊觉不称也。‘无趣’,即自嫌形秽之意”(施鸿保语),并以东晋高僧支道林的才、惠远的德来称誉赞公。“白㲲巾”,西域白㲲布做的手巾(详仇注)。后半截写傍晚雨景,别饶韵致。张彦远《名画记》载,大云寺东浮图有三宝塔,东壁北壁郑法轮画,西壁田僧亮画,外边四壁杨契丹画。《画断》载,吴道子尝画殿内五龙,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云雾。有谓“图画”指山、“龙鳞”指松,或谓二者统指山林远色,皆非。还是施鸿保理解的对:“上句乃统言所画,下句则言道子画龙,天阴尤觉鳞皆润也。”
其三:“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天黑闭春院,地清栖暗芳。玉绳迥断绝,铁凤森翱翔。梵放时出寺,钟残仍殷床。明朝在沃野,苦见尘沙黄。”写通宵不寐所见所闻所感。黄生说:“夜景无月最难写,惟杜写无月之景,往往能入妙。‘夜深殿突兀’,摹写逼真,亦在暗中始觉其然耳。以后句句是暗中说话。”老杜《夜宴左氏庄》写无月夜景亦佳。鲍照《代夜坐吟》:“冬夜沉沉夜坐吟,含声未发已知心。霜入幕,风度林。朱灯灭,朱颜寻。体君歌,逐君音。不贵声,贵意深。”谢灵运《夜宿石门》中这几句:“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都凭听觉写夜景,殊觉可喜。“金琅珰”,指长锁(见《汉书·西域传》注),或指殿角悬铃之声,均可。“铁凤”见《西京赋》:“凤?翥于甍标,咸溯风而欲翔。”薛综注:“谓作铁凤凰,令张两翼,举头敷尾,以函屋上,当栋中央,下有转枢,常向风如欲飞者。”“心清”“地清”二句不仅“清”字复,意亦重,但“闻妙香”见“心清”,“栖暗芳”见“地清”,着眼点一在情一在境,情境自别,就不觉字复意重了。才享几日清福,明朝又将重返乱世尘沙中厮混,篇末不觉感叹系之了。
其四:“童儿汲井华,惯捷瓶在手。沾洒不濡地,扫除似无帚。明霞烂复阁,霁雾搴高牖。侧塞被径花,飘飖委墀柳。艰难世事迫,隐遁佳期后。晤语契深心,那能总钳口?奉辞还杖策,暂别终回首。泱泱泥污人,㹞㹞国多狗。既未免羁绊,时来憩奔走。近公如白雪,执热烦何有?”此叙早起惜别之情。头四句言小童汲井,动作熟练,洒扫庭院,轻而易举。“明霞”四句写阁映朝霞、窗销宿雾、繁花被径、垂柳拂阶的绮丽晨景。“艰难”四句慨叹世路艰难,惜未趁早归隐;一向钳口结舌,今得倾诉衷肠。《九辩》:“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左传》哀公十二年:“国狗之瘈,无不噬也。”旧注多以为是时贼将张通儒收录衣冠,污以伪命,不从者杀之,老杜晦迹寺中,故有“那能总钳口”,及“泥污人”“国多狗”等语。(31)最后四句是说,我既然一时摆脱不了羁绊,我还要常到这里来走动、歇憩;因为您就像白雪,挨近您,我内心那热辣辣的烦躁情绪,自会烟消云散的。根据“开复闭”“尘沙黄”“泥污人”“国多狗”等语揣测,大概那几天风声较紧,老杜官小人微,虽暂疏约束,也不能不提防恶狗乱咬,故来寺院,小作勾留,借以晦迹;今见风势似已稍减,只得辞离清净佛地,重入尘沙乱世,但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临路踟蹰。——这组诗,不是也多少反映了老杜陷贼、困居长安时的一个生活侧面么?(32)
这一时期他经常饿饭,全靠朋友们周济度日。他的《雨过苏端》说:
“鸡鸣风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无食起我早。诸家忆所历,一饭迹便扫。苏侯得数过,欢喜每倾倒。也复可怜人,呼儿具梨枣。浊醪必在眼,尽醉摅怀抱。红稠屋角花,碧委墙隅草。亲宾纵谈谑,喧闹慰衰老。况蒙霈泽垂,粮粒或自保。妻孥隔军垒,拨弃不拟道。”久旱下雨就好。困居长安,生活没有着落,只好一早起身,拄着藜杖,拖泥带水地到熟人家混口饭吃。一般的交情,叨扰一顿也就不好再去了,只有这位“文章有神交有道”的苏端却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令我倾倒之至。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他也是可怜人,可是见我来了,总是叫儿子弄点梨枣什么的来款待我,陪我饮酒谈心。这时节屋角的花开得很稠,墙边的草长得绿油油的。亲朋们聚在一起纵谈笑谑,嘻嘻哈哈的,这欢乐的气氛感染了我,仿佛自己也年轻了。老天降下甘霖,今年粮食兴许有希望。想起妻儿子女远隔军垒真教人难过;咳,还是抛到一旁,就别提了。——这诗写得真率有味,既见老杜当时的穷愁苦恨,也见他处逆境而能维持精神上的平衡,不丧失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情味和美的敏感。施鸿保说:“君方蒙尘,家方寄食,在常人亦未能恝然,况公之至性过人耶?”只身陷贼,哪能“恝然”?不过,若片面地认为他处于此时此境,必然终日愁苦,了无生趣,那也算不得是真的懂得老杜、懂得人生啊。浦起龙说:“‘红稠’‘碧秀’,亦为雨色点染。”北方干燥,何况春旱,即使花开草长,也蒙着一层尘土;一经大雨洗净,才更觉其“红”其“碧”了。杨伦说:“杜诗只字片句,后人多据为故实。山谷诗:‘月黑虎夔藩’,谬误可笑。东坡《送梁左藏诗》云:‘东方健儿虓虎样,泣涕怀思廉颇将’,乃用杜《遣兴诗》中语,亦恐非原文。不如放翁诗:‘无复短衣随李广,但思微雨过苏端’,为新而工也。”放翁此联,得来现成,不但有韵致,且饶兴寄,颇佳。
《喜晴》大概作于这场春雨初晴时:“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肃肃春增华。青荧陵陂麦,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干戈虽横放,惨淡斗龙蛇。甘泽不犹愈,且耕今未赊。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谁疵瑕。英贤遇?轲,远引蟠泥沙。顾惭昧所适,回首白日斜。汉阴有鹿门,沧海有灵查。焉能学众口,咄咄空咨嗟!”“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就是“久旱雨亦好”的意思。二诗同时所作,话语不觉讲得如此相似。久雨初霁,出郭眺望,只见桃李花开,麦苗青青,春景固然佳丽,但诗人心里想的却是:下了这场及时雨,今年的收成没问题,我饿肚子的日子该有个完了吧?《义山杂纂》中以“看花泪下”等九事为“杀风景”。老杜面对大好春光,不但寄希望于麦秋,还急盼桃李结实疗饥,这无疑是大杀风景了。但处如是境,作如是想,便如实道来,乱世人心情立见,真切感人。次言雨后正好耕种,丈夫虽尽出征,妇女在家,虽不能种植黍稷,犹得侍弄菜麻。退一步作宽慰语,其实是慨叹遭乱而农事多荒,“我饥岂无涯”的愿望终难实现。于是就引出了末段伤乱而欲远遁的意思,结束全篇。“出郭眺西郊”“回首白日斜”,出城回城,独往独来,老杜身虽陷贼,行动仍然是相当自由的。老杜从长安逃出是在这年四月,这次出郭闲游就在出逃前不久。要是说这次出游是为出逃探路,看看是否出得去,是否有隙可乘,恐怕也不是毫无道理。《杜臆》说:“前引‘商山芝’‘东门瓜’,后引‘鹿门’‘海查’,语似复而意不同;前就古人说,后就自己说。谓决意远去,无之而不可,陆有鹿门,海有灵查,未尝阻我往也。”王嗣奭不是早就看出老杜当时已下决心要逃走了么?
正在这个时候,被俘虏到洛阳的郑虔潜回长安。老杜与他相遇于郑潜曜驸马家池台,悲喜交集,同饮赋诗说:
“不谓生戎马,何知共酒杯。燃脐郿坞败,握节汉臣回。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别离经死地,披写忽登台。重对秦箫发,俱过阮宅来。留连春夜舞,泪落强徘徊。”(《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老杜前在长安与郑虔过从甚密,据《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等诗,可见二人交谊之深。大概从老杜移家奉先之后,他俩便不常见面了。不想大难同经,出生入死,今又重逢于旧游地,契阔谈宴,听歌观舞,春夜留连,真是喜出望外,喜极生悲,不能自已。汉末董卓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万岁城。后吕布杀董卓,陈尸于市,天气开始炎热,董卓素来肥胖,油脂流了一地,守尸吏点火放在他的脐中,光明达旦。安禄山也很肥胖,腹垂过膝,每着衣带,须三四人相助,两人抬起肚子,让亲随李猪儿用头顶着,然后才能取裙裤带或系腰带。这年正月,严庄和安庆绪合谋,命李猪儿以大刀砍安禄山的肚子,肠数斗流于床上而死。事与董卓相类似,所以用在这里很恰当,且能借以表达深恶痛绝的感情。《新唐书·郑虔传》载:“安禄山反,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伪授虔水部郎中,因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老杜见郑虔陷贼能有这样的表现,今又乘间脱归长安,自以为难能可贵,就用苏武仗节牧羊、终于归汉的故事来称赞他。“白发”二句写郑虔陷贼忧心如焚、须发尽白而中情可察。“秦箫”用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萧史、日于楼上吹箫作凤鸣事。老杜初入长安时,常在长安神禾原郑驸马家莲花洞游赏、宴会,曾作《郑驸马宅宴洞中》诗。这次又来此饮酒听乐,所以说“重对秦箫发”。据《新唐书·公主传》和独孤及《郑驸马孝行纪》载,玄宗女临晋公主嫁郑潜曜在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大历时卒;郑潜曜当驸马后“嗣荣阳郡公,佩金印,列长戟,垂三十载”,当卒于大历四年(七六九)左右。长安沦陷时,郑潜曜如果来不及随玄宗出逃而留了下来,不降,必会像霍国长公主和王孙、驸马那样遭孙孝哲杀害;降了,两京收复后必会像陈希烈、张垍驸马那样不被处死即遭流放。郑潜曜终身富贵,到大历四年才去世,且以孝友著称,入《新唐书·孝友传》。可见他早已逃离长安,当时不在城中,所以得以保全性命与人格,未受叛乱的牵累。郑虔是郑潜曜的叔叔,杜甫是郑府的老熟人:“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林。”他俩来了,即使驸马爷不在,留下来看家的主事人等自会设宴款待、奏乐娱宾的。《晋书·阮籍传》附阮咸传载阮籍与兄子阮咸居道南,诸阮居道北。“俱过阮宅来”,即用此典点明二郑是叔侄关系。“秦箫”“阮宅”泛指郑驸马家,不一定表明郑驸马本人当时就在场,仇兆鳌说:“此诗当做于至德二载之春。是年正月,安庆绪杀安禄山,故诗中有‘燃脐’句。想此时贼党稍纵,降官、郑(虔)得回京也。”言之有理。既然降官、郑虔他们能从东京逃归长安,难道一向不受重视、行动较为自由的未入流的兵曹参军杜甫就不可能逃出长安吗?就在这次喜遇郑虔于郑驸马池台后不久的四月中,老杜终于从金光门逃出,历尽千辛万苦,间道窜归凤翔,结束了这一段惊变与陷贼的苦难历程。
(1)详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稿上篇》,冯至《杜甫传》采此说。
(2)《旧唐书·史思明传》载:“(史思明)与安禄山同乡里,先禄山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禄山岁日生。”仅大一天,却隔了一个年头。按虚岁计算,史思明大安禄山一岁。又同传载:“天宝初,(史思明)频立战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尝入奏,玄宗赐坐与语,甚奇之。问其年,曰:‘四十矣。’”案:天宝二年(七四三)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宠待甚厚,谒见无时(见《资治通鉴》)。既云史思明入朝天宝初,当亦在是年。此时史思明自称年四十,则可推知史思明约生于中宗长安四年(七〇四),安禄山生于神龙元年(七〇五)。《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安禄山被杀于至德二载(七五七)正月,卒年五十余。据推知生年计算,卒年当为五十三,证以“五十余”,足见无大讹。
(3)《旧唐书·史思明传》载:“(史思明)与安禄山同乡里,先禄山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禄山岁日生。”仅大一天,却隔了一个年头。按虚岁计算,史思明大安禄山一岁。又同传载:“天宝初,(史思明)频立战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尝入奏,玄宗赐坐与语,甚奇之。问其年,曰:‘四十矣。’”案:天宝二年(七四三)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宠待甚厚,谒见无时(见《资治通鉴》)。既云史思明入朝天宝初,当亦在是年。此时史思明自称年四十,则可推知史思明约生于中宗长安四年(七〇四),安禄山生于神龙元年(七〇五)。《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安禄山被杀于至德二载(七五七)正月,卒年五十余。据推知生年计算,卒年当为五十三,证以“五十余”,足见无大讹。
(4)此据《资治通鉴》,其余诸书所载各有不同,详司马光《考异》。
(5)《资治通鉴》载:“(天宝十载,正月)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内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6)浦起龙说:“三章,写到击敌之事,纯用虚机,而含讽之旨,即从此露出。其章法更屈曲出奇。以‘重守’剔‘重勋’,主意提破矣。‘英主’‘出师’,本是直接,却下‘岂知’二字,便无显斥之痕。‘亘长云’下,宜接‘遂使’句矣,却用‘六合’两句,横鲠其中,又隐然见此举之多事。且‘孤军’下,似宜用‘重高勋’意作一转落,却又直接‘遂使’一句,此中又有无限含蓄。”指出这诗故意寓深意于条理不甚通畅的文字之中,颇得作者用心。
(7)此据《资治通鉴》。《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冬十一月,反范阳,诡言奉密诏讨杨国忠,腾榜郡县,……燕老人叩马谏,禄山使严庄好谓曰:‘吾忧国之危,非私也。’礼遣之。因下令:‘有沮军者夷三族!’”
(8)《读杜心解》说:“又有名士评此诗,执五章‘跃马二十年’句,以二十年前燕将系张守珪,遂谓前三章诗不指禄山。此无论前事无关,公不必寄诸咏叹。即使五诗两橛,有是体否?彼直认‘良家子’为实有是人耳,不知此诗特赋家所谓东都宾、西都主人,皆托言也。则是‘二十年’者,亦泛言黩武之久也,何胶柱若是?说杜纷纷,徒增霾雾,冤哉!”
(9)据诗中所述,此斋地势甚高,或即以“高”为斋名。施鸿保认为这里的“高斋”乃“泛言,非实有斋名高也”。
(10)《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哥舒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协,上常和解之,使为兄弟。是冬(天宝十一载),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于城东。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为其忘本故也。兄苟见亲,翰敢不尽心!’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尔!’翰欲应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阳醉而散,自是为怨愈深。”安禄山所指即此等事。
(11)《读杜诗说》:“注:重表,盖有两重表亲。今按诗云:‘我之曾祖姑,尔之高祖母’,是即重表之义。盖姑之子为表兄弟,由姑而上,祖姑之子孙,则重表矣;由祖姑而上,不得云再重表,故但以重表统之,犹同姓兄弟叔侄,共祖以上,皆称从也。注误。”其说甚是。
(12)旧注以为“左冯翊,同州也。天宝末,公避寇同州。按同州即奉先”。奉先亦属同州,且杜甫也曾寄寓该县,谓“同州即奉先”不为大错。但据前所述,潼关未破前杜甫已携家由奉先北徙白水,当指白水为是。
(13)《晋书·王戎传》载:“(王戎)尝与群儿戏于道侧,见李树多实,等辈竞趣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戎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这里的“苦李”只是用典,泛指路旁不能取食的野果,不必拘看。
(14)旧注有的以为孙宰是三川县宰(令),有的以为是人名。玩味诗意,作人名为是。
(15)朱鹤龄说:“古人招魂之礼,不专施于死者,公诗如‘剪纸招我魂’‘老魂招不得’‘魂招不来归故乡’‘南方实有未招魂’,皆招生时之魂也。”宋人蔡梦弼却说:“剪纸作旐,以招其魂,不必果有此事,只是多方安慰耳。”湖南新宁解放前有为受惊的人叫魂的迷信习俗。杜诗中既多次写到招生魂之事,恐非虚指。蔡说不足信。
(16)王嗣奭说:“结之曰:‘谁能艰难际,豁达露心肝?’何等激切!读此语知‘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乃述孙宰语,所谓‘露心肝’也。宰本故人,盖述昔日交契之厚,非此日才发誓也。且文势亦顺。注云:‘夫子’指孙宰。误。”
(17)《鄜州图经》载鄜州治洛交县(今陕西富县),羌村,洛交村墟。《元和郡县志》载隋开皇十六年,分三川、洛川二县,置洛交县。《述怀》:“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旧注:“三川在鄜州南,公之家寓焉。”这理解是错误的。这诗作于老杜从沦陷的长安逃往凤翔时。他陷贼困居长安时所作《月夜》说:“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称“鄜州”,就州治而言。称“三川”,因州治所在的洛交县系分三川旧地,且近三川之故,并非其家先住三川,再徙鄜州羌村。如果这一时期内真搬了一次家,老杜从陷贼到作《述怀》时一直未得家书,他也无从得知:“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他得家书是在写《述怀》之后:“去凭游客寄,来为附家书。今日知消息,他乡且定居。”(《得家书》)诗中称其家寄寓之地或“鄜州”,或“三川”,或“羌村”(见《羌村三首》),虽用三名,实指一地:鄜州洛交县境内三川旧地的羌村。
(18)四川文史馆《杜甫年谱》认为,杜甫过延州时,暂住州城南七里的小河。小河又名南河,源出牡丹山,山产牡丹甚多,樵者以为薪,又名牡丹川。宋时又名杜甫川,以杜甫尝避乱居此故名,范仲淹曾大书“杜甫川”三字于川口,见《陕西通志》。可参看。
(19)旧注谓至德二年五月,朝廷自清渠之败,以官爵收散卒,凡应募入官者,皆衣金紫,此所谓“奴仆旌旄”。仇兆鳌按:“此诗作于元年之冬,尚未见此事。卢注云:公陷贼时,方冀朝廷将士反正不暇,岂得以‘奴仆旌旄’辄为讥弹?当是指贼党如田乾真、蔡希德、崔乾祐之徒,各拥旌旄耳。”“奴仆且旌旄”犹《后出塞》其四中的“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仇、卢所论甚是,惟谓此诗作陷贼时则不足据。
(20)黄鹤注:“诗云‘两京三十口’,又云‘烽举新酣战’,当是天宝十五年。”
(21)元好问《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等诗庶几近之。
(22)《旧唐书·房琯传》载;“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新唐书》所载大致相同。可见中使促战在陈涛斜遇敌两军对垒之时、大败之前。朱鹤龄以为中使促战在陈涛斜既败之后、房琯领中军再战之前。恐非。当然,第二次出战致败,也可能出于中使的督促。房琯书生不解事,难免不败,有人掣肘,败得更快更大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李隆基父子则异于是。父信杨国忠谗言,遣中使促哥舒翰决战,招致潼关之败。子亦复遣中使促战,招致陈涛之败。小人有罪,中使有罪,主将有罪,皇帝就没有罪么?
(23)李东阳《麓堂诗话》;“唐士大夫举世为诗,而传者可数。其不能者弗论,虽能者亦未必尽传。高适、严武、韦迢、郭受之诗,附诸杜集,皆有可观。子美所称与,殆非溢美。惟高诗在选者,略见于世,余则未之见也。至苏端,乃谓其文章有神,薛华与李白并称,而无一字可传,岂非有幸不幸邪?”可参看。
(24)《旧唐书·常衮传》载其事较详:“(衮)与杨绾同掌枢务,代宗尤信重绾。绾弘通多可,衮颇务苛细,求清俭之称,与绾之道不同。……绾寻卒。衮与绾志尚素异,嫉而怒之。有司议谥绾为文贞。衮微讽比部郎中苏端,令驳之。毁绾过甚,端坐黜官。”可见苏端是常衮的人。常衮虽无大恶,而其德望、政事,逊杨绾远甚。
(25)我家乡湖南新宁县老辈子人讲话,犹谓客人为“人客”。
(26)王建《赠王枢密》就说明他所知宫闱秘事都是听王守澄说的:“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小时。脱下御衣先赐著,进来龙马每教骑。长承密旨归家少,独奏边机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得外人知?”《唐诗纪事》载:“建初为渭南尉,值内官王枢密者,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复怀轻谤之色。忽过饮,语及汉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乃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后为诗以赠之,乃脱其祸。”
(27)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宫词》其八十三:“新教内人供射鸭,长将弓箭绕池头。”与此意近。
(28)据《汉书·外戚传》载,汉成帝既立赵飞燕为皇后,后宠少衰,而飞燕女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然《三辅黄图》载成帝赵皇后居昭阳殿。后人多以昭阳属飞燕,如沈佺期《凤箫曲》:“飞燕侍寝昭阳殿,班姬饮恨长信宫。”
(29)张戒《岁寒堂诗话》:“杨太真事,唐人吟咏至多,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黩之耶?惟杜子美则不然。《哀江头》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不待云‘娇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专宠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绝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时行乐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辇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不待云‘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时行乐可喜事,笔端画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题云《哀江头》,乃子美在贼中时,潜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连昌宫词》在元微之诗中,乃最得意者。二诗工拙虽殊,皆不若子美诗微而婉也。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这段话,封建意识严重,见解冬烘,不足取,但为了说明《哀江头》《长恨歌》二诗优劣,举出了一些具体诗句作比较,若光就艺术表现而论,却也不无道理。
(30)陈鸿《长恨歌传》:“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可见《歌》和《传》是二人根据传闻同时分别创作的。
(31)施鸿保最反对这种说法:“《大云寺赞公房四首》,注:黄鹤编在至德二载陷贼中作,以诗有泥污人、国多狗、尘沙黄等句也。今按泥污人,第言雨后泥泞,第二云:‘雨泻暮檐竹,风吹春井芹。’第四云:‘明霞烂复阁,霁雾搴高牖。’当是晚雨夜阴,晓乃开霁,故虑归途泥泞污人。国多狗,亦是破晓归来,市廛未启,犹惊狗吠,国多者,因《左传》国狗字,偶拈用也。尘沙黄,尤是市廛语。注又引鲍昂说:是时贼将张通儒,收录衣冠,污以伪命,故云泥污人、国多狗。此亦曲说;伪命污人,尚非可比之泥污,贼众掳京,亦非只多狗而已。细玩四首,并无一语及乱事。若陷贼时作,则身方被拘,岂能游宿僧房,优游自适?且君方蒙尘,家方寄食,在常人亦未能恝然,况公之至性过人耶?四首似未可定何时作,黄鹤亦凭臆编耳。”施说理由也不很充分:一、老杜当时并非大名人,他被俘之后送到长安,未授任何伪命,行动较为自由,既能“春日潜行曲江曲,……欲往城南望城北”,怎见得就不可以到大云寺“时来憩奔走”呢?二、《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雨过苏端》等诗都作于陷贼时,这些诗中也说:“千里犹残旧冰雪,百壶且试开怀抱。”“苏侯得数过,欢喜每倾倒。”“浊醪必在眼,尽醉摅怀抱。”同是一个老杜,难道就不允许他为了遣愁解闷,到大云寺来优游几天,跟赞公和尚倾诉一下在外头讳莫如深的心里话:“晤语契深心,那能总钳口?”封建学者过于强调老杜的一饭不忘君,忠诚出于天性,致使一些议论往往迂腐可笑。三、“到扉开复闭”“苦见尘沙黄”“那能总钳口”“泱泱泥污人,㹞㹞国多狗”,说得多蹊跷!显然是有慨于时事而又不敢明言的话,鲍昂诸人的理解是正确的,并非曲说。施鸿保无视这些“语及乱事”的句子而宣称“无一语及乱事”,这若不是“骑驴寻驴”的迷糊,定然是故意不认账的狡狯了。当然《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确乎是明显地“语及乱事”;但这些篇章,可以记在心里,也可以写在纸上收藏着,不必张扬。能要求送人的《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也是那样彰明较著地“语及乱事”么?
(32)四川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说:“最后,杜甫决意投奔凤翔,临行前,却往怀远坊大云经寺住宿数日,以避胡人耳目。寺僧赞公以青丝履及白㲲巾见赠,并索题诗。诗遂言及‘把臂有多日’,并言‘晤语契深心,那能总钳口?奉辞还仗策,暂别终回首。泱泱泥污人,㹞㹞国多狗。’以诗意为据,可见其晦迹寺中时,与赞公密商潜投凤翔之计,而戒以勿泄漏消息,恐遭国狗之噬也。”理解有所不同,录以备考。
相关阅读
文章标题:在相濡以沫的日子里-杜甫的惊变与陷贼
链接地址:http://www.shootiniron.com/jianjie/795.html
下一篇:喜达行在-杜甫长安遁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