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旅病年侵”-杜甫潇湘夕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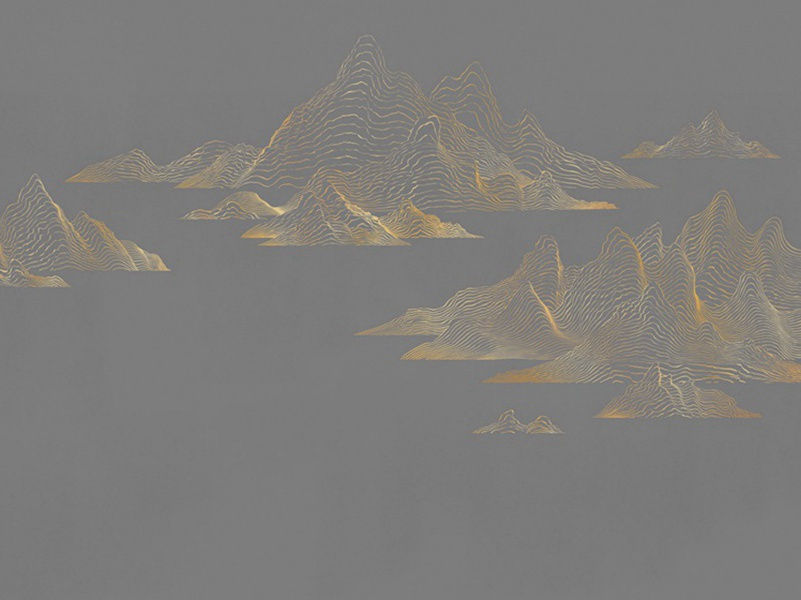
老杜阻水停泊方田驿,幸得聂令附书致酒肉疗饥,尔后复至县呈诗面谢,前后经过,诗及长题记之甚悉,本无疑义。岂意身后即为好事之徒编造出宰致牛酒、杜饮食过量、一夕而卒于耒阳的传说。此说唐郑处诲载之较早较完全:“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明皇杂录补遗》)又韩愈《题杜工部坟》:“今春偶客耒阳路,凄惨去寻江上墓。……招手借问骑牛儿,牧儿指我祠堂路。……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子美当日称才贤,聂侯见待诚非喜。洎乎圣意再搜求,奸臣以此欺天子。捉月走入千丈波,忠谏便沉汨罗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贤所归同一水。……坟空饫死已传闻,千古丑声竟谁洗!”(《集注草堂杜工部诗外集·酬唱附录》)亦载牛酒饫死之说,但表示怀疑,以为这是聂令为搪塞天子搜求而胡诌出来的谎话,而杜甫其实同屈原、李白一样,都是淹死的。(37)蔡梦弼案:“此退之题杜工部,惟见于刘斧摭遗小说,韩昌黎正集无之,似非退之所作。然大历、元和,时之相去,犹未为远,不当与本集抵牾若是,乃后之好事俗儒,托而为之,以厚诬退之,决非退之所作也明矣。”从艺术风格上看,这诗也不像出自韩愈手笔。故不得据此以为牛酒饫死之说中唐时已有之。戎昱有《耒阳溪夜行》,题下原注:“为伤杜甫作。”但萧涤非先生已考证出此诗实为张九龄所作,所谓“自注”为后人伪托(详《文史哲》一九八五年第五期所载《〈耒阳溪夜行〉的作者是张九龄—它不可能是杜甫死于耒阳的“铁证”》),很可信,故亦不足为凭。到了晚唐,崔珏《道林寺》谓杜饥寒厄死于耒阳:“白日不照耒阳县,皇天厄死饥寒躯。”(《文苑英华》卷三四二)裴说诗一首提及白酒寒江之恨:“皇天高莫问,白酒恨难平。悒怏寒江上,谁人知此情。”孟宾于诗一首也说:“一夜耒阳雨,……白酒至今闻。”(钱注本引自《耒阳祠志》)其余如郑谷《送田光》“耒阳江口春山绿,恸哭应寻杜甫坟”(《郑守愚文集》)、罗隐《经耒阳今杜工部墓》“旅魂自是才相累,闲骨何妨冢更高”(《甲乙集》)、曹松《哭陈陶处士》“白日埋杜甫,皇天无耒阳”(《曹松诗集》)、齐己《次耒阳作》“因经杜公墓,惆怅学文章”(《白莲集》)等等,无不谓杜甫卒、葬于耒阳。可见耒阳杜墓无论真假,早为士林所公认,所以来此凭吊、题咏的,到晚唐以后就很多。既然当时社会上大多这样认为,这就无怪乎新旧《唐书》的作者习而不察,竟误采小说家言入杜甫传了。旧传说:“(甫)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新传只删去“永泰二年”这一明显的错误,又把“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改为“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显得“醉死”比“撑死”高雅些。其余文字虽有所简练,而内容基本不变。可见他们都不怀疑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其实这是不可信的,北宋的王得臣早在《麈史》中已根据有关杜诗加以订正说:“(大历)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乱,仓皇往衡阳,至耒阳,舟中伏枕,又畏瘴,复沿湘而下,故有《回棹》之作。末云:‘舟师烦尔送,朱夏汲(及)寒泉。’又《登舟将适汉阳》云:‘春色(宅)弃汝去,秋帆催客归。’盖回棹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继之以《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云:‘北归冲雨雪,谁悯弊貂裘。’则子美北还之迹,见此三篇,安得卒于耒阳耶?要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按元微之子美墓志称:‘子美孙嗣业,启子美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拜余为志,辞不能绝。’其系略曰:‘严武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殡岳阳。’近时故丞相吕公为《杜诗年谱》云:‘大历五年,辛亥,是年还襄汉,卒于岳阳。’以前诗及微之之志考之,为不妄,但言是年夏,非也。”尔后耒阳一案,仍不免时有聚讼(38),而从是说者居多,因所述行踪凿凿有据,教人没法不相信。
老杜并未在耒阳撑死或淹死,不久因不耐此间溽暑,亟思北归襄汉,就决计不去郴州,而掉转船头,顺流北返了。其时作《回棹》(39)说:
“宿昔试安命,自私犹畏天。劳生系一物,为客费多年。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散才婴薄俗,有迹负前贤。巾拂那关眼,瓶罍易满船。火云滋垢腻,涷雨裛沉绵。强饭莼添滑,端居茗续煎。清思汉水上,凉忆岘山巅。顺浪翻堪倚,回帆又省牵。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几杖将衰齿,茅茨寄短椽。灌园曾取适,游寺可终焉。遂性同渔父,成名异鲁连。篙师烦尔送,朱夏及寒泉。”仇兆鳌说:“前《咏怀》诗云‘衣食相拘阂’,即所云‘劳生系一物’。赵注谓劳生之人,不免系著一物,是也。钱笺云系一物,言此生犹一物耳。于下句不相接。”薛梦符说:《茶录》:潭邵之间渠江中有茶乡,人每年采撷,其色如铁,芳香异常。黄希说:昔尝官郴,见其风土唯尚煎茶,客至继以六七,则知“茗续煎”者,湖南多如此。《襄沔记》:王粲宅在襄阳岘山坡下,宅前有井,人呼为仲宣井。老杜《一室》:“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即咏此。这诗前半谓厌此间之热而欲回棹,后半谓欲托迹襄阳而终老:平素我本想随地自安,因为贪图安逸总怕老天不照看。可不其然为了谋生之故,客旅他乡一年又一年。(40)更何况衡岳湖湘间盛夏酷热多病、世俗人情浇薄,前贤绝迹不至而我独来,真有负前贤了。巾拂不过是为了修饰仪容,在船上又没人瞧,天这么热正好不用;镇日只顾饮酒解愁,空瓶空罍倒很容易堆满一船。火云烤出一身脏汗,暴雨能稍起沉疴。勉力加餐,莼羹性寒堪解暑;闲坐无聊,只好连续煎茶喝。想到汉水之上的清幽和岘山之巅的凉爽,我决计回祖籍襄阳去。顺水的波浪反可依凭,转帆北去又可省去拉纤。我家当阳君那一立岘山一沉万山潭的纪绩碑至今不坏(详上卷六页),王粲宅前的古井依然存在。我回到那里将赖几杖扶老,寄迹于短椽茅屋之中。抱瓮灌园意在取适,常游佛寺有终焉之志。我将遂性退隐如同沧浪渔父,决不学那功成不受赏而取名的鲁仲连。
老杜回到潭州,暂时住了下来,到秋天,才准备携家乘船去汉阳(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西)、襄阳。作《登舟将适汉阳》说:
“春宅弃汝去,秋帆催客归。庭蔬犹在眼,浦浪已吹衣。生理飘荡拙,有心迟暮违。中原戎马盛,远道素书稀。塞雁与时集,樯乌终岁飞。鹿门自此住,永息汉阴机。”老杜去年春梢来潭寓居,故曰“春宅”。秋帆催客北归,我即将抛弃你这所从去春就寄寓的宅子而去。庭中的蔬菜还满眼青葱,别浦的风浪已在吹拂征衣了。飘荡各地生计笨拙不堪,有心济世可惜到老无成。中原戎马倥偬,远道很少有信来。塞雁列阵征空尚有春秋之期,而樯乌却整年随着船飞。《庄子》载汉阴丈人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从此我将效庞德公归隐鹿门,永息机心。
这时前后,同他一起避地同谷县(今甘肃成县)的李衔(详第十二章第二节)路过长沙,他们相逢即别,老杜作《长沙送李十一衔》说:
“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久存胶漆应难并,一辱泥涂遂晚收。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西康州”即同谷县。老杜以乾元二年(七五九)冬寓同谷,至今年(七七〇)为“十二秋”。《同谷七歌》其七“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即写二人当日相濡以沫之情,而老杜入蜀发同谷时,“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发同谷县》),这送行的“数子”中就有李衔在。岂料十二年后重逢仍在客中,这无疑会令他不胜感叹了。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后汉陈重、雷义交谊至笃,时人语曰:“胶漆虽坚,不如雷陈。”“泥涂”,犹言草野。比喻卑下的地位。《左传》襄公三十年:“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容斋四笔》:“汉太尉李固、杜乔,皆以为相守正,为梁冀所杀。故掾杨生上书,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归葬。梁冀之诛,权势专归宦官,倾动中外。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有帝欲不谛之语,桓帝得奏震怒,逮云下北寺狱。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下延尉,皆死狱中。其后襄楷上言,亦称为李杜。灵帝再治钩党,范滂受诛,母就与之诀曰:汝今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谓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时著名,故韩退之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凡四李杜云。”《诗薮》:“李白、杜甫外,杜审言、李峤结友前朝,李商隐、杜牧之齐名晚季,咸称李杜,是唐有三李杜也。又杜赠李衔有‘李杜齐名真忝窃’之句,衔亦当能诗耶!”这诗前半叙前次别后情事,后半感李相知之深而惜重逢即别:当年共寓同谷,不期十二年后又在长沙重逢。郎官遥受,终愧未蒙赐履入朝;这里究竟不是我的故土,所以就懒得登楼。你待我情同胶漆,义气过人;可叹我久辱泥涂,穷老莫振。古今“李杜”并称的不一而足,可我真不敢同你齐名;对此朔云寒菊,就越发增添我的别绪离忧。朱瀚说:“云菊离忧,别景别情,一语尽之。”李子德说:“浑朴有初唐气味。”
到了暮秋,一切准备就绪,即将解缆北归,作《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说:
“水阔苍梧野,天高白帝城。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大府才能会,诸公德业优。北归冲雨雪,谁悯敝貂裘?”顾注:旧解谓“苍梧”“白帝”,皆公经历之地。公实未尝至苍梧。此言湘江之水甚阔,直接苍梧。《潭州图经》谓其地有舜之遗风。白帝司秋,盖言暮秋时令,如《望岳》诗云“高寻白帝问真源”。唐时巡属诸州,以节度使府为“大府”。黄生说:起法何等阔大!三句虽用阮籍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事,然哭字又取湘江染泪意,故贴首句为精。四句以衰候映老景,故贴次句。后半意言亲友虽多,其能悯此敝貂裘冲雨雪而北归者谁乎?结处字字应转前半篇,章法精审。话虽这么说,这首诗写得不算太出色,但能见出他当时的心境,仍有参考价值。
秋尽冬来,老杜抱病躺在潭州开往岳阳的船上,百感交集,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首段说:
“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滞淫。鼓迎方祭鬼,弹落似鸮禽。”《汉书·律历志》:黄帝使伶伦取竹于嶰谷,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鸣,其雄鸣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孔子家语》: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枚乘《七发》: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使琴挚斫斩以为琴。“半死心”,借琴自况。《杜臆》:“公时将适汉阳,而于潭、岳则在东北,故‘舟泊常依震’,盖先天东北方之卦(为震)也。马融《长笛赋序》云:‘有洛客舍逆旅吹笛,融去京师逾年,暂闻甚悲。’公去京久,故云。”王粲《登楼赋》:“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老杜病肺畏热,故用其语。头年作《北风》“气待北风苏”“且知宽病肺”,《江汉》“秋风病欲苏”可证。《汉书·吾丘寿王传》:“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颜师古注:“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岳阳风土记》:岳州地极热,十月犹单衣,或摇扇,震雷暴雨,如中州六七月间。又:荆湖民俗,岁时会集,或祷祠,多击鼓,令男女踏歌,谓之歌场。《庄子·齐物论》:“且汝亦大(太)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鸮炙。”时夜,谓鸡。鸮炙,谓炙鸮鸟(猫头鹰)为食。这段从风疾叙起,接写湖中行船所见所感:轩辕黄帝制出的律管且把它收起来,虞舜弹过的五弦也撤下去吧!我身患风疾已不再能演奏,还错将雄管当作雌管吹,听到弹出变了调的琴声伤透了我半死的心。古代圣贤的名声何其邈远,羁旅他乡病情一年比一年加重。船往汉阳每晚总停泊在东北的震方,湖面平阔很早就能见到报晓的参星。我苦忆京华如同马融闻笛,迎风凭眺若开王粲之襟。遥望寒空,悲故乡不见;群云惨淡,生岁暮层阴。从迷茫的雾气中露出水乡的茅屋,红叶枫林的岸后便是重叠的青山。冬天里炎方的瘴气仍然郁积不消,濛濛的细雨又总是下个不停。咚咚的鼓声,报道迎神歌舞刚开场;弓响弹落,似乎打下了土著爱烤着吃的猫头鹰。二段说:
“兴尽才无闷,愁来遽不禁。生涯相汩没,时物正萧森。疑惑樽中弩,淹留冠上簪。牵裾惊魏帝,投阁为刘歆。狂走终奚适?微才谢所钦。吾安藜不糁,汝贵玉为琛。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叨陪锦帐坐,久放白头吟。反朴时难遇,忘机陆易沉。应过数粒食,得近四知金。”《晋书·乐广传》:“尝有亲客,久阔不复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于时河南听事壁上有角弓,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复置酒于前处,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顿愈。”按《风俗通·怪神》记应郴请杜宣饮酒,杯中有形如蛇,宣得疾,后于故处设酒,蛇乃弩影。其事相同。后遂以“杯弓蛇影”比喻因疑虑而引起恐惧。辛毗谏,魏文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扬雄被收,本为刘歆子棻狱辞连及,今云“为刘歆”,借以趁韵。《说苑·杂言》:“七日不食,藜羹不糁。”庾信《哀江南赋序》:“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赋云:“天意人事,可为凄怆伤心者矣。”《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典略》:“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庄子·则阳》:“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陆地无水而沉,比喻隐于市朝中。也比喻不为人知,有埋没之意。张华《鹪鹩赋》:“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后汉书·杨震传》:王密怀金遗杨震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这段因漂泊而回顾往事:尽兴观赏刚刚忘了烦闷,谁知忽然又愁苦难禁。这主要是想到一生流离道路,眼下的景物又是这样的萧条。杯弓蛇影,疑畏多端因而得病;朝簪不缺,淹留各地却难归京。我曾为救房公廷诤忤旨,有如牵裾惊魏帝的辛毗;又像是受刘歆之子狱辞连累而投阁的扬子云。我这么奔走窜逐终将何往?微才谬承诸公所钦真令我感谢不尽。我倒安于喝不加糁子的野菜羹,你们诸位真说得上是“其人如玉,为国之琛”(晋代马岌铭宋纤壁语)。我那个随身携带的破乌皮几(详第十五章第十一节)缝了又缝,百结鹑衣更是补丁摞补丁。我的哀伤同庾信一样的深沉,不草书檄却有异于陈琳。十个暑天穿的都是岷山产的葛衣,霜期三度听厌了楚户的砧声。我曾做郎官叨陪锦帐(郎官有锦帐,见《汉书·百官志》),如今已有许久没摇晃着白头自长吟。反朴还真的时代难以遇到,若能做到忘机便易“陆沉于俗”(东方朔语)。只因为不能没有超过鹪鹩数粒的粮食,于是就强颜接受诸公清白得来的赠金。三段说:
“春草封归恨,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苏张舌,高夸周宋镡。纳流迷浩汗,峻址得嵚崟。城府开清旭,松筠起碧浔。披颜争倩倩,逸足竞骎骎。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魏晋南北朝士大夫喜欢服食一种烈性药物,叫五石散(一名寒食散),服食后须漫步以散发药性,叫作“行药”,也叫“行散”。鲍照有《行药至城东桥》诗。唐时还有行药的风气。除这诗写到外,元稹的《春病》也有“行药步墙阴”之句。潘岳《西征赋》:“夭赤子于新安,坎路侧而瘗之。”今年四月臧玠杀崔瓘作乱,老杜携家从长沙城中逃出时,有“犹乳女在旁”。“瘗夭追潘岳”,或即指此女早殇(41)(详本章第九节)。《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行,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成玄英疏:“寿陵,燕之邑;邯郸,赵之都。弱龄未壮,谓之余子。赵都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国少年远来学步。”按《汉书·叙传上》引《庄子》,“学行”作“学步”。后因以“邯郸学步”比喻摹仿别人不成,反而丧失固有的技能。曹丕《与吴质书》:昔伯牙绝弦于钟期,痛知音之难遇。《庄子·说剑》:天子之剑,以周宋为镡。这段叙留滞湖南,感幕府亲友关照:原先满以为“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哪知前年春大出峡却仍然回不去。那么,最好让萋萋春草将思归的愁恨封闭起来。(42)可是来到湖南,又“多忧污桃源”(《咏怀二首》其二),寻不到栖遁之地。这就只得像转蓬般四处飘零,沿途还须服药行散,却没法减轻沉重的病情。跟在潘岳的后面,掩埋了早殇的幼女;真想到邓林中去寻找夸父扔掉的那根手杖,扶持我越过世途的艰险。可笑我邯郸学步拙于随俗,最感激诸公对我的知遇之恩。你们借来苏秦、张仪三寸不朽之舌,过高地夸奖我是天子剑上的周宋之镡。纳入众流的三江五湖浩汗无涯,高地之上更耸立着高高的山峰。城府的大门冲着朝阳敞开,苍松翠竹掩映着清清的流水。人们都带着倩倩的笑脸,骑着骎骎的快马来投奔诸公。你们都具有慧眼能赏识像我这样既愚且直的人,惟愿皇天后地能照临我感激诸公的赤诚。末段说:
“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仇注:“公孙恃险”,应指蜀中事。永泰元年,崔旰杀郭英乂,据成都。大历四年,杨子琳杀夔州别驾张忠,据其城。“侯景未擒”,臧玠失讨也。《南史》:侯景与慕容绍宗战,败渡淮,绍宗追之,景使人谓之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臧玠杀崔瓘,三州刺史合兵讨之,杨子琳受赂而还,与绍宗之纵侯景无异,故云“未生擒”。曹丕《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其二:“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虞人之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载《左传》)《晋中兴书》:葛洪止罗浮山中炼丹,在山积年,忽与广州刺史邓岱书云:“当欲远行。”岱得书,狼狈而往,洪已亡,时年八十一,颜色如平生,体亦软弱,举尸入棺,其轻如空衣,时咸以为尸解得仙。尸解,言将登仙,假托为尸以解化。这段叹战乱不息而伤己之将卒于道路:蜀将割据,仿佛公孙述仍在恃险;杨子琳受赂而还,当今的侯景所以就未被生擒。洛阳久无信来,长安还未解除战争的威胁。畏人、问俗,到处可忧;战血、军声,南北伤乱。像许靖的远去交州(详本章第四节《咏怀二首》其二评注),这已非我的体力所能胜任;自知定如葛洪的尸解,将死途中。若论家事,空有丹砂诀而炼不成金,思想起来,不觉泪如雨下。仇兆鳌说:“此诗作于耒阳阻水之后,其不殒于牛肉白酒明矣。但云‘葛洪尸定解’,盖亦自知不久将殁也。编年者当以此章为绝笔。”这确乎是老杜的绝笔,也是他预为自己草就的行状和祭文。张惕庵说:“此亦杜集大文章,曾子易箦之词,留守渡河之志。”千载以下,读之犹令人感动不已。
而今而后,我们再也读不到老杜的新诗了。不久,他终于走完了他艰难苦恨的人生历程,怀着忧国忧民的莫大悲痛,割舍了陪伴他流离道路、苦难同经的杨氏夫人,抛下他那些旅泊异乡、谋生乏术的弱男幼女,在这年冬天,赍志而没于潭岳途中。他身后境况的凄凉可想而知,幸亏四十年后宗武之子嗣业请元稹作《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虽简而粗存梗概。叙曰:
“……适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之为文,拜余为志。辞不能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系曰:
“……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以家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余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铭曰:
“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呜呼!千载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43)。”而叙中如下一段评价杜诗的文字,则恰可借来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1)浦起龙说:“鹤云:自岳州之潭州作,是也。按自岳而南至潭,自应入湖。但南岳更在湖南。题曰《过南岳入洞庭》,旧注以为过而后入。仇氏遂以前八为过南岳,中八为入洞庭。诗义、图经,两相背戾矣。不知‘过’者将然之事,‘入’者现在之事。题意盖谓将欲过彼,故入此湖也。”
(2)仇注:“孤舟防盗,故须宿依农畔;水程夜泊,故闻驿报更筹。”似是而非。其余诸注,亦未尽善。
(3)旧注引《方舆胜览》:青枫浦在潭州浏阳县。樊文考杜甫在湖南行踪,不曾亦不可能入浏阳河(或醴陵河)到浏阳。湘江流经长沙南北一带,两岸多枫树(杜甫湖南诗中也多处写到枫),这一带以枫为名的地方也颇多,故双枫浦可能是当时长沙、湘潭一带湘江岸边的一个小地名,惜今已无考。
(4)仇兆鳌串讲说:“言停舟枫浦,见双树久摧,自从衰谢以后,人但惊其精力已竭,又谁道未衰之先,材堪栋梁乎?今兀立江干,浪高而枫顶微露,似浮纱帽,波平而皮藓半呈,如截锦苔。其摧朽若此,我欲问江边地主,借作上天浮槎,庶不终弃于无用耶。”解“浪足”句等稍嫌穿凿,仍能自圆其说,可参看。
(5)仇注:“呀坑”者,淤坑,如口之呀开。“坑”,一作“吭”。蔡注:“呀吭”,乃滩口。
(6)黄鹤注:当是大历四年春初到潭州时作。
(7)樊文疑题中“岳”字衍。
(8)“塔劫”的“劫”通级。
(9)王嗣奭说:“此七言排律,一气抒写,如珠走盘,阅者不知,而类编者不入排律何耶?”邵子湘说:“排比绵丽,子美七古,此又为变调,盖永叔、子瞻之滥觞也。”前者以为是七排,后者以为是七古。
(10)樊文对此诗曾着重加以探讨,并提出假说,现简介于后备考:白马潭所在地,旧注有说在潭州的,无据也无可考;魏泽一《试论杜甫在湖南作诗的编次问题》(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三辑)仅据湘阴县有白鸟潭,便怀疑白马潭即白鸟潭之“夺误”亦不足据信;有的则只说岳州巴陵县有白马矶(或口或湖),可是既未能确指其地,也未说明与白马潭有何相关。旧注都引《水经注》:“江水又东,径彭城口(矶),北对隐矶,二矶之间有巨石,孤立大江中,其江东浦世谓之白马口。”《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七将其地列入岳州府,并说“白马口亦谓之白马矶”。经查有关地志,其地在岳州巴陵县东北长江东岸,亦即长江流经今临湘县那一段的中间。如王琦注李白诗引《湖广通志》就说“白马矶在岳州临湘县北十五里”(县志作“十里”,皆依旧县治陆城),清嘉庆、同治修《临湘县志》则记载说在县东北十里(“十里”,是;“东北”当为北)。白马矶是指那块江中巨石,白马口指矶旁的江东浦,而白马潭则在白马矶下,并说其地“磴道险仄”,与李白《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所述“遇憩裴逸人,岩居陵丹梯”的情况亦合。这里唐时有裴隐隐居于此。隐曾官侍御,与李白、贾至有交往。李白流夜郎至江夏,应隐之约,“期月满泛洞庭”,曾来白马矶相访,有诗记其事。杜甫发白马潭、入洞庭湖再到岳阳时写有一首《陪裴使君登岳阳楼》诗,这个“裴使君”或即裴隐,此时似已出牧岳州,故杜甫称他为“使君”。李白于肃宗乾元元年(七五八)流夜郎途中经洞庭湖(贾至于此年贬为岳州司马),至大历三年(七六八)正好十年,裴隐或尚在。裴隐与李白、贾至相好,李白、贾至与杜甫相好,基于这种关系,杜甫大历三年冬至岳阳后与之相识,得到照顾,乃是情理中事。杜甫初到岳阳时正值隆冬,又一路劳累,体弱多病,裴隐便把他安排到自己在白马矶的居所去住,这也是很可能的,杜甫在白马矶住到春节过后,天气转暖了,便决意南行,于是就从白马潭登船出发,写了《发白马潭》一诗,宣布南征就此开始。
(11)前采清明前后老杜已到长江的说法,那么发长沙宿凿石浦当在清明以后。而此云“仲春江山丽”(仇注更据“阙月”句定此诗作于大历四年二月初),何耶?可见有关时地的考察与作品的编次未尽妥帖:(一)清明前后在长沙,(二)凿石浦在长沙以南,(三)此句中之“仲春”,三者必有一误。
(12)《杜臆》:“飘风不敢系舟,则舟子固须操舟,而舟中之人俱须助力,故云‘宾从劳’。”
(13)樊文:《嘉庆县志》卷三说,其地有“山塘坳,合马家坳水入于湘”,故又名凿石塘,诗中“回塘澹暮色”句,显然是眼前景的实写。
(14)仇注:就中原而言,湖南为边徼之地。
(15)《哀王孙》亦有“可怜王孙泣路隅”“已经百日窜荆棘”云云,可参看。
(16)颜延之《和谢监灵运》:“尽言非报章,聊用布所怀。”“报章”即指和诗。
(17)朱鹤龄说:襄州襄阳郡,乃山南东道节度使所治。广德初,梁崇义据襄州,代宗不能讨,因拜山南东道节度,至建中元年始为李希烈所诛。则“梁公”即崇义。史称其以地褊兵少,法令最洽,折节遇士,自振襄汉间。观此诗所称“襄阳幕府天下异,主将俭省忧艰虞”,又云“粱公富贵于身疏,号令明白人安居”,其语正与史相合。
(18)诗中有“秋晚岳增翠”之句可证。
(19)诗中有“我丈特英特,宗枝神尧(指唐高祖)后”之句可证。
(20)《旧唐书·代宗本纪》作“瓘”,《新唐书·代宗本纪》《资治通鉴》作“灌”。两《唐书·崔瓘传》俱作“瓘”。
(21)仇注:“诗止七韵,而题云八韵,用韵取耦,不取奇也。”
(22)钱注本有“近”无“递”,仇注、浦解本有“递”无“近”;《镜铨》本作“递近”,恐出于臆定,但较醒豁,姑从之。
(23)《杜臆》:“……盖追述前日饯裴赴道州事。而群公之内,似苏亦预焉,故云‘宴筵曾语苏季子’。”
(24)《诗薮》:“‘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吴均、何逊之精思。‘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阴’,庾信、徐陵之妙境。‘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高华秀杰,杨、卢下风。‘冠冕通南极,文章落上台。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典重冠裳,沈、宋退舍。‘耕凿安时论,衣冠与世同。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寓神奇于古澹,储、孟莫能为前。‘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含阔大于沉深,高、岑瞠乎其后。‘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花动朱楼雪,城凝碧树烟’,王右丞失其秾丽。‘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李太白逊其豪雄。至‘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则钱、刘圆畅之祖。‘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则元、白平易之宗。‘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卢仝、马异之浑成。‘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鸥饥’,盂郊、李贺之瑰僻。‘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岛、可幽微所从出。‘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籍、建浅显所自来。‘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义山之组织纤新。‘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用晦之推敲密切。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见者。”从来龙去脉着眼论证杜诗的集大成,未必尽当,亦颇有所见。
(25)浦起龙说:“于王则泛称才德,于敬则寄意招魂。盖亦绝意还乡,弥思远去之苦衷耳。旧说以‘招魂’为招蜀州之魂,非也。”浦说虽可通,但不一定就对。
(26)五年前偶与迦陵先生谈到此诗。我说,年来我眼老花,始觉“雾中看”三字描状之切。迦陵以为,老眼看花,并不如在雾中,恐眼有他异。事后验光,得知我左眼视力果衰退。今(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迦陵将枉驾蜗居,不觉忆及此事。因思老杜当年,除患消渴、肺气、耳聋诸疾外,眼或亦有病。
(27)《唐宋诗举要》高步瀛案:“浦辨龟年开元前何必不在京,其说殆是。至据《壮游》诗‘出游翰墨场’为往来岐宅崔堂,则实傅会不足信。岐王似以嗣王珍为是,崔九亦当指崔氏旧堂。黄、仇说是,浦氏谓杜公十四五巳日游王公间,谬矣。”如此即是,不一而足,岂能无言!《唐音癸签·集录三》载:《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崔五(九)云云。岐王薨于开元十四年,崔五(九)涤亦卒于开元中,时子美方十五岁。天宝后子美又未尝至江南。他人诗无疑。”上古秦汉时所谓“江南”和唐开元二十一年所置“江南西道”,无不包括湖南在内。老杜在湖南前后三年,且卒于此,岂得谓“天宝后子美又未尝至江南”?此说更是无稽。
(28)赵次公说:“言寡妻平日遭扰,自从崔太守为郡之后,如兀足者之安于堵墙之下,不复惊动也。”此另一解。仇兆鳌按:“寡妻有两说:《诗》‘刑于寡妻’,此在位之妻;潘岳诗‘夫行妻寡’,此民间寡妇。”
(29)《九域志》:郴州西北至衡州界一百三十七里。则郴在衡之东南。地理上以东为左。故云“左郴岸”。
(30)仇注:《说文》:亭邮表。徐曰:表,双立为桓。今邮亭立木交于其端,或谓之华表。原句中“云鸟阵”旧作“云鸟埤”。公诗“共说总戎云鸟阵”,作“阵”字是。言华表之旁,皆列云鸟之阵。焮案:古代亦在桥梁、宫殿、城垣或陵墓等前设华表以为标志和装饰。多为石柱,柱身往往雕有蟠龙等纹饰,上为云板和蹲兽。北京天安门前后就有两对华表。
(31)张衡《西京赋》:“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洛阳伽蓝记·城东龙华寺》:“里有土台,高三丈,上有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罢市,谓散去市集。又酒楼亦称“旗亭”。
(32)该诗六句“伤於(于)”一作“商於”。黄鹤说:“商於”,即张仪欺楚之地,唐为商州上洛郡。史云大历三年三月,商州兵马使刘洽杀防御使殷仲卿。此为仲卿而作。朱鹤龄说:鹤说似有据,但三年春,公自峡之江陵,商於在江陵西北,不当云“白马东北来”。考《九域志》,衡州北至潭州三百九十里,公自潭如衡,则所见之白马为自东北来明矣。臧玠与达奚觏忿争,是夜以兵杀瓘,所谓“中夜伤于战”也。梦弼、次公皆主此说。
(33)仇兆鳌说:“李公官方素著,必能变通出奇,其所谋画,岂同凡算?断不使王室终微,贼徒恣横也。”说有不同,可参看。
(34)此采仇兆鳌说:“‘三千徒’,与读书声相应,言文德宜足销乱,而声带杀伐者,时经臧玠之乱也。《杜臆》:下二句,暗用子路鼓瑟,有北鄙杀伐之音。”浦起龙说:“(此段)见文教之兴,足以销弭兵气。言何必生徒众多,始能销乱?似此深林‘苍翠’之中,凉井‘辘轳’之畔,一闻‘书声’,而杀气渐衰息矣。‘仿佛’,作稀微将止之义解。此正与首段相照。”理解有所不同,可参看。
(35)仇注:“‘延归望’,国学难见。‘减愁思’,州学新成。”恐非原意。
(36)浦起龙说:“题又云‘至县’,则是受馈成诗后,仍登岸至县呈谢。”又于题“聂令”下加注:“题当止此,下疑小注原文,盖以注明阻水之处耳。”如此,则“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当就耒阳县城而言,“舟行一日”指平时坐船须一日之程。
(37)此说详唐人李观《杜诗补遗》:公往耒阳,聂令不礼。一日过江上洲中,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为惊湍漂没,其尸不知落于何处。洎玄宗还南内,诏天下求之,聂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子美为牛肉白酒胀饫而死,葬于此矣。”仇兆鳌引此,复加按语说:“此欲雪牛酒饫死之冤,而反加以水淹身溺之惨。子美何不幸罹此奇祸!且考泰陵升遐,以及少陵逝世,其间相去十载。《补传》颠倒先后,是全不见杜诗年次者。元宾博雅人,岂肯为此不根之说乎?此必后人伪托耳。”
(38)如钱谦益即坚持旧说:“《旧书》本传:甫游衡山,寓居耒阳,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元稹墓志: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公卒于耒阳,殡于岳阳,史志皆可考据。自吕汲公《诗谱》不明旅殡之义,以谓是年夏还襄汉,卒于岳阳。于是王得臣、鲁訔、黄鹤之徒,纷纷聚讼,谓子美未尝卒于耒阳。又牵引《回棹》等诗,以为是夏还襄汉之证。按史:崔旰杀郭英乂,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此大历三年也。是年至江陵,移居公安,岁暮之岳阳,明年之潭州,此于诗可考也。大历五年夏,避臧玠之乱,入衡州。史云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以卒。《明皇杂录》,亦与史合。安得反据《诗谱》而疑之?其所引《登舟》《归秦》诸诗,皆四年秋冬潭州诗也,断不在耒阳之后。《回棹》诗有‘衡岳’‘蒸池’之句,盖五年夏入衡,苦其炎暍,思回棹为襄汉之游而不果也。此诗在耒阳之前明矣。安可据为北还之证乎?以诗考之,大历四年,公终岁居潭。而诸谱皆言是年春入潭,旋之衡,夏畏热,复还潭,则又误认《回棹》诗为是年作也。作年谱者,臆见猜度,遂奋笔而书之,其不可为典要如此。吾断以史志为证,曰:子美三年下峡,由江陵、公安之岳;四年之潭;五年之衡,卒于耒阳,殡于岳阳。其他支离傅会,尽削不载可也。当逆旅憔悴之日,涉旬不食,一饱无时,牛肉白酒,何足以为垢病!而杂然起为公讳,若夫刘斧之摭遗小说,韩退之、李元宾之伪诗、伪传,三尺童子皆知笑之。而诸人互相驳正,以为能事,又何足道哉!”黄生以为其说大有可议者,驳之甚中肯綮:“予按:微之墓志,出于公孙嗣业之请,一当以此为据。史文则撮取《杂录》与墓志而成,即其末云:‘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已与志相抵牾。又况公以大历五年避臧玠之乱入衡,史书公卒乃在永泰二年。竟以武薨、蜀乱、公去成都、下峡、出江陵、过湖南,皆作一年之事,则其疏略纰缪、不可据信亦已明矣。若以卒耒殡岳,两存其实,则二地悬绝,更隔洞庭一湖,卒此殡彼,理不可信。何独《明皇杂录》为与史合而确据之也?详史所书牛酒饫死之说,实采之《杂录》。《录》叙此事而终之云:‘今集中犹有赠耒阳诗。’即此勘破作者正因此诗,饰成其事,小说家伎俩毕露。今顾谓《杂录》与史合,岂知史正承《录》谬耶?观‘牛肉白酒’四字,显是此诗题中‘书致酒肉疗饥荒江’之句文致而成。诸家辩之固当,而反谓其曲为公讳,观钱之意,不过欲确明其卒于耒阳,不难尽扫诸家之说耳。然本传既难凭信,元志述公事虽略,犹赖‘旅殡岳阳’四字,幸存一线,为《回棹》《登舟》《发潭》《过湖》诸诗左证,而顾必为耒阳争一杜公之遗蜕,其智不反出宋人下哉?予独惜此书有功于子美,而贻此挂漏,为通人之一蔽也。”此二说最有代表性,录以备考。
(39)此诗旧编在大历五年。黄鹤疑诗中不言臧玠之乱,当是四年至衡州,畏热将回棹欲归襄阳,不果而竟留于潭。仇兆鳌按:“杜诗凡纪行之作,其次第皆历然分明,不当以欲行未果之事载之诗集。考臧玠之乱在四月,公往衡山过耒阳俱在夏日。此云‘火云垢腻’,殆耒阳回棹而作。词不及忧乱者,前后诸诗已详,不必每章叠见也。还依旧编为当。”樊维纲说:“既言‘回棹’,当然是由南而北了。诗中有‘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句,衡阳东傍湘江,北背蒸水,知此诗为由衡州北回时作。杜甫在湖南三年中由衡州北回有两次,一次在大历四年投韦之晋扑空后,时在春梢;一次是在大历五年耒阳阻水后,时在盛夏。诗中有‘火云’‘涷雨’二句,据旧注,火云,夏日旱气也;涷雨,夏日暴雨也。从时间上说,与大历五年那次情况相合。黄鹤注本以此诗未言及臧玠之乱,便编在大历四年,浦注本从之,谓为‘四年夏畏热北回之作’。这在时间上都是说不过去的。其他旧注本编于大历五年应是可从的。”从时间上加以判断,这一条补充论证很有说服力。仇注本于《回棹》后编入《过洞庭湖》:“蛟室围青草,龙堆隐白沙。护堤盘古木,迎棹舞神鸦。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槎。”复加按语说:“《潘子真诗话》:元丰中,有人得此诗刻于洞庭湖中,不载名氏,以示山谷,山谷曰:‘此子美作也。’今蜀本收入。大历四年夏,公在潭州,此当是五年夏自衡州回棹,重过洞庭湖而作。今据郑卬编次为正。或疑公卒于耒阳,不应又作此诗,不知耒阳之卒,原未可凭,而此诗之精练,非公断不能作。”“破浪”句是夏景,既然夏过洞庭,何以暮秋仍在潭州赋诗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臆断难凭,姑附录于此,不入正文。
(40)浦注:“‘安命’,本欲随地自安也。‘自私’者,贪安之谓。‘畏天’,畏天之不与我安也。是何也?为‘系物’谋生之故,长此‘劳生’耳。‘为客费年’,即所为‘劳生’者。”译文采此说。
(41)黄鹤以“瘗夭”为葬宗文:“元稹《墓志》云:‘嗣子宗武,病不克葬’,则宗文为早世矣。考大历二年熟食日有诗示宗文宗武,是明年出峡,二子尚无恙也。意是年春自潭之衡时,乃丧宗文。公在衡畏热,舟复回潭,故下句又用渴死事。公与聂令有旧,当是瘗宗文于耒阳,后人遂误以为公坟耳。”仇兆鳌按:“宗文若卒于耒阳,应有哭子诗,集中未尝见,亦黄氏意拟之词耳。”老杜散佚篇什不少,今集中未尝见哭子诗,亦不足证其必无,仇氏用来反驳的理由不充分。现既推断出“瘗夭”为葬其幼女,则黄氏意拟之词就很难成立了。
(42)仇注:“刘安《招隐》:‘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封’,犹增也。”说亦通。只是采此解即成眼前景,与时令不合。
(43)据元稹《墓系铭并序》所载,杜甫墓当在今河南偃师。此外尚有三墓:一在今湖南耒阳,一在今湖南平江,一在今河南巩县。四墓真伪,至今聚讼纷纭,可从长探讨,但都寄托了后人缅怀杜甫的无限深情,都应受到同样的重视和保护。《访古学诗万里行》记述四墓颇详,可参看。
相关阅读
文章标题:“羁旅病年侵”-杜甫潇湘夕霁
链接地址:http://www.shootiniron.com/jianjie/916.html
上一篇:赞学与谢馈-杜甫潇湘夕霁
下一篇:身世的传说(杜甫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