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气吹沅湘”-杜甫潇湘夕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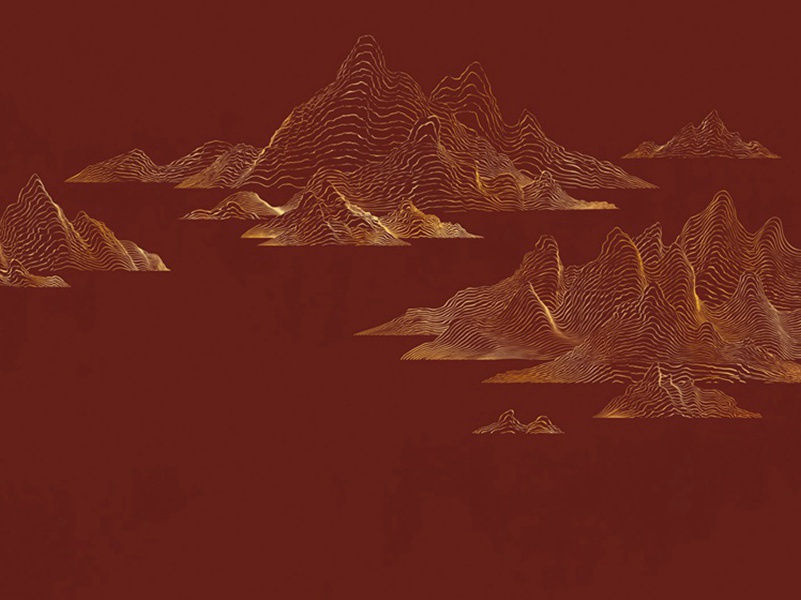
今年(大历五年,七七〇)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观察使崔瓘,据潭为乱。老杜携家避乱入衡州,且欲由衡赴郴,依舅氏崔伟。作《入衡州》,首叹安史乱后叛变频仍:
“兵革自久远,兴衰看帝王。汉仪甚照耀,胡马何猖狂!老将一失律,清边生战场。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汤。重镇如割据,轻权绝纪纲。军州体不一,宽猛性所将。”“汉仪”,喻唐法。“胡马”,指安史。“失律”,谓潼关不守。“清边”,谓四方俱扰。“忍瑕垢”,谓主忧臣辱。“空金汤”,谓两京俱陷。“重镇”,指河北叛将。“轻权”,慨制御无术。“体不一”,各自为政。“性所将”,不奉朝命。发端二句意谓国运兴衰主要看帝王的行事如何。接着便历数衰世的种种变化和危机,虽未明言,亦可窥见诗人有不满于先帝时君行事之意。次叹崔瓘贤而死于兵乱:
“嗟彼苦节士,素以圆凿方。寡妻从为郡,兀者安堵墙。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库实过防。恕己独在此,多忧增内伤。偏裨限酒肉,卒伍单衣裳。元恶迷是似,聚谋泄康庄。竟流帐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发中夜,高烟燋上苍。至今分粟帛,杀气吹沅湘。福善理颠倒,明征天莽茫。”《旧唐书·崔瓘传》载:“崔瓘,博陵人也,以士行闻。莅职清谨,累迁至澧州刺史,下车削去烦苛,以安人为务,居一年,风化大行,流亡襁负而至,增户数万。有司以闻,优诏特加五阶,至银青光禄大夫,以甄能政,迁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瓘到官,政在简肃,恭守礼法。将吏自经时艰,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历五年四月,会月给粮储,兵马使臧玠,与判官达奚觏忿争。觏曰:‘今幸无事。’玠曰:‘有事何逃?’厉色而去。是夜,玠遂构乱,犯州城,以杀达奚觏为名。瓘惶遽去,逢玠兵至,遂遇害。代宗闻其事,悼惜久之。”“苦节”,指崔。“圆凿方”谓崔正直而不能应变。“寡妻”四句,见崔能克己爱民:“寡妻从郡”,谓崔无姬妾之好;“兀(刖足)者安堵”,能使残疾者得所。(28)“旌麾”六句,言崔不能恤军:“旌麾非任”,领军非其所长;“府库过防”,吝于赐予;“恕己”而不治人(《三略》“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致令将士不满,崔因此而“多忧”;“限酒肉”“单衣裳”,克扣将士惯例所应得。“元恶”,指臧。“迷是似”,借缺饷以惑众听。“泄康庄”,泄愤于衢路。“竟流”六句,记入夜叛军烧杀掠夺的暴行。“颠倒”,谓崔不应死。“莽茫”,谓臧不应存。老杜亲身经历了这次叛乱,所记富于真实感,对崔瓘的评价也比史传全面。素称其作为“诗史”,原来他真具“史才”啊!次叙仓卒避乱再入衡州:
“销魂避飞镝,累足穿豺狼。隐忍枳棘刺,迁延胝趼疮。远归儿侍侧,犹乳女在旁。久客幸脱免,暮年惭激昂。萧条向水陆,汩没随渔商。报主身已老,入朝病见妨。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刚肠。参错走洲渚,舂容转林篁。片帆左郴岸,通郭前衡阳。华表云鸟阵,名园花草香。旗亭壮邑屋,烽橹蟠城隍。”躲着飞箭走把魂都吓掉了,穿过豺狼般的叛军逃命真累了两条腿。隐忍着僻处的枸橘刺扎,脚上打起泡了还得挣扎着走。儿子陪着从城里绕远道儿回到一向寄寓的船上,妻子领着那个还没断奶的小女儿走在身旁。久客他乡幸得脱险免祸,自惭年老无力讨贼内心激动不已。悄悄地向着水陆洲边奔去,躲到船上且随渔商漂泊。可叹我想报主此身已老,想入朝又受到疾病的妨碍。那就只好悠悠荡荡地随俗浮沉,郁郁不乐地任刚肠百转。乘着船驶过参差错落的大小沙洲,离潭州远了便从从容容地转过片片竹林。扯起风篷驶向东南的郴州(29),之前先来到了衡阳。华表旁排列着云鸟阵(30),名园里的花草正芳香。旗亭(31)高耸市容壮观,城墙的望楼(橹)上已设置了烽燧以备战。——这一段记叙半夜兵变老杜从城里逃上船的情形,以及沿途和到达衡州时的所见所感,很具体很有意思。《杜臆》说:“逃难而兼携妻孥,尤见其苦,而以得免为幸。”(仇注引,今本异)从所述携妻孥逃难的苦况看,他家当时还是住在长沙城中的。可能是他总想北归,行李、长物多放在长期包用的船上,人也不妨住上去,要是有条件租到房子,他们还是会住在城里的。案: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载:“(甫)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老杜同夫人感情甚笃,集无悼亡诗,他作中亦丝毫不露鼓盆之戚,可见杨氏当卒于后,且较老杜小十岁有余(开元二十九年他们结婚时杜甫三十岁,杨氏当在十九岁左右)。那么,假定头几年杨氏养了个老闺女,还惯着她一直没断奶(在旧社会,几岁的孩子还吃奶,并不罕见),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在前面将“犹乳”句译成:“妻子领着那个还没断奶的小女儿走在身旁。”《读杜诗说》:“此云‘犹乳女’,则公晚年又生一女也。后《风疾舟中》诗:‘?夭追潘岳’,或即此女早殇。潘岳诗,亦殇女也。”可参看。当然这句也可以译成:“那个还在奶孩子的女儿走在身旁。”这样一来,就变成是《北征》中那个“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的“痴女”在奶孩子了。从“北征”到“入衡州”已有十四年,那“痴女”现今也该有十八九岁了。只要嫁了人,这也同样是有可能的啊!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由老杜率领的“水上吉卜赛家族”,不仅有夫有妻有弟有儿女,还有女婿、外孙子,成员不少,转移起来也就更不方便了。次记衡州刺史杨济,而兼及苏涣,喜御敌有人:
“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岩廊。扶颠待柱石,独坐飞风霜。昨者问琼树,高谈随羽觞。无论再缱绻,已是安苍黄。剧孟七国畏,马卿四赋良。门阑苏生在,勇锐白起强。问罪富形势,凯歌悬否臧。氛埃期必扫,蚊蚋焉能当?”《旧唐书·代宗本纪》载:臧玠据潭州为乱,澧州刺史杨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杨济出军讨玠。东汉光武帝改御史长史为中丞,与尚书令、司隶校尉,朝位皆专席而坐,京师号“三独坐”。“风霜”,御史之任。杨济兼御史中丞,今协同讨玠,故“中有”八句首赞之:城中这位有古人风的杨刺史,他是最卓越的廊庙大才。他扶颠济危为国柱石,朝班独坐凛凛威风。我昨日来此,与他并坐,犹如蒹葭倚玉树;又听他高谈阔论,陪着干了一杯又一杯。且不说他对我一再表示难分难舍的情意,他早已安下我那颗仓皇失措的心。剧孟,西汉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以“任侠”闻名,在河南地区势力很大。吴楚七国之乱时,汉将周亚夫将至河南闻吴楚等叛乱势力未与他勾结,认为“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子虚》《上林》《哀二世》《大人》四赋。白起(?—前二五七),一称公孙起。战国时秦国名将。郿(今陕西眉县)人。秦昭王时从左庶长官至大良造。屡战获胜,夺得韩、魏、赵、楚的很多土地。秦昭王二十九年(前二七八)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因功封武安君。长平之战大胜赵军,坑杀俘虏四十多万人。后为相国范雎所妒忌,意见不合,被逼自杀。仇注:“苏涣少喜剽盗,善用白弩,巴蜀号为白跖,故以剧孟、白起比之。又公称其诗云‘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时’,故以马卿四赋比之。旧注以剧孟、马卿比刺史,非也。阳(杨)济身为重臣,可云剧孟乎?时涣亦自潭州奔衡,公望当事收而用之,及阳(杨)济不能用,故又走交广而罹罪耳。”“问罪”四句,是说澧、道、衡三州刺史联兵讨贼问罪,形势大好,敌我臧否悬殊,相信必奏凯歌,扫净妖氛,蛟蚋焉能抵挡?末思郴州舅氏崔伟,并及张劝,欲往依亲友:
“橘井旧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怨暑雨,厥土闻清凉。诸舅剖符近,开缄书札光。频繁命屡及,磊落字百行。江总外家养,谢安乘兴长。下流匪珠玉,择木羞鸾凰。我师嵇叔夜,世贤张子房。柴荆寄乐土,鹏路观翱翔。”今湖南郴州市东五里有苏仙岭。相传西汉文帝时苏耽在此成仙,故名。“橘井”四句想郴州风土。《元和郡县志》载郴州东半里有苏耽旧宅遗迹。“诸舅”,犹诸侯、诸生,虽一人亦可称“诸”。此指其二十三舅郴州录事崔伟(见前赠诗)。“剖符近”,指崔摄州事。续述崔多次寄书相招。《陈书·江总传》:江总七岁而孤,依于外氏。幼聪敏,有至性。舅吴平光侯萧劢,名重当时,特所钟爱。《晋书·谢安传》:谢安寓居会稽,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此以江自况,以谢誉崔。“下流”二句意谓凤凰非梧桐不栖,而避地有同择木,但自愧非凤凰耳。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借喻己性疏懒而不能偶俗。“世贤”句下原注:“彼掾张劝。”《资治通鉴》载:建中四年(七八三)十一月,德宗在奉天,陕虢观察使姚明扬,以军事委都防御副使张劝,去诣行在。劝募兵得数万人。甲申,以劝为陕虢节度使。张确有才干,以张子房称之,也并非毫无根据。“乐土”,指郴州。“鹏路翱翔”,仇、浦二氏以为意谓崔、张将有事功。杨伦从旧说,谓末句仍合到衡州,“言将寄居郴土,以观衡守之讨贼立功,翱翔鹏路也”。《钱注杜诗》《读杜心解》均编此首入古诗类。王嗣奭却说:“此亦五言排律,总叙目前情景,而一机流走,绝无滞碍。”杨伦说:“此诗多用偶句,似古亦似排,与《桥陵诗》同格。”
他同时前后又作《逃难》说:
“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哀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前四句回忆从前的逃难。王嗣奭说:“代宗上元二年,公五十,时东川节度使段子璋反,崔光远牙将花敬定斩之;而兵不戢,遂大掠,故公率妻子而逃。始则京师乱而逃蜀,既自北而南。今南又乱而逃,故云‘南北逃世难’。”中六句记目前逃臧玠作乱之难。仇兆鳌说:“此暮年衰病,又挈妻子而逃也。曰‘四海’,曰‘万里’,见随地皆乱矣。‘回首悲叹’,起下‘故国’‘邻里’。”末叹泪尽湘岸、无家可归。据此,则可断定此诗当作于避臧玠之乱时。《杜臆》因“五十白头翁”句而遽编此诗于上元二年,并解末句说:“终当出三峡之楚之湘江,乃吾泪尽之处也。”《杜诗镜铨》因邵子湘说此诗“凡浅,定是赝作”而附于集外。均非定论,不足为据。
《白马》也是当时为臧玠之乱而作(32):
“白马东北来,空鞍贯双箭。可怜马上郎,意气今谁见?近时主将戮,中夜伤于战。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仇兆鳌说:此为潭州之乱死于战斗者,记其事以哀之。马带箭而来,则马上者见害矣。“丧乱死多门”一语极惨:或死于寇贼,或死于官兵,或死于赋役,或死于饥馁,或死于奔窜流离,或死于寒暑暴露;惟身历患难,始知其情状。带箭伤马负死未离鞍战将急驰而来。——起得突兀,令人骇异不止。
过了几天,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杨(阳)济,筹划联兵讨臧之事有进展,但也出现些新情况。老杜作《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首段说:
“愧为湖外客,看此戎马乱。中夜混黎甿,脱身亦奔窜。平生方寸心,反当帐下难。呜呼杀贤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没齿埋冰炭。”就中原而言,潭州在洞庭湖以外。这段抒逃难感愤:惭愧我远客湖南,又亲眼得见这场兵乱。半夜里城中突然一片混乱,我也幸得脱身逃窜。可叹他崔公真心为民,反为部下所忌终于遭难。贤良被杀,却无人起来将兵灾驱散。我自恨不是救世的英雄,却终身愤恨不平就像胸怀冰炭。二段说:
“耻以风病辞,胡然泊湘岸。入舟虽苦热,垢腻可溉灌。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这段因船中苦热而聊以自遣:我耻以老病辞官,如今何以还停泊在湘江之岸。住在船上虽然热得很,身子脏了倒可就近洗洗涮涮。可怜那横尸路边的遇难者,形骸旦夕间就会完全改变。三段说:
“中丞连帅职,封内权得按。身当问罪先,县实诸侯半。士卒既辑睦,启行促精悍。”《礼记》:“十国以为连,连有帅。”这段嘉许阳中丞兴师讨罪:中丞您身居连帅之职,境内有乱您权重足以按察。您身当问罪联军之先,因为南中军州大半受您统辖。各地士卒既已结集,精锐的部队马上就要出发。四段说:
“似闻上游兵,稍逼长沙馆。邻好彼克修,天机自明断。南图卷云水,北拱戴霄汉。美名光史臣,长策何壮观!”“上游兵”,指道州刺史裴虬所率之师。道州居湘水上游。这段喜裴道州领兵会讨:听说上游的部队,已逼近长沙驿馆。邻州刺史既能如此很好配合,中丞您临事自当明断。祝诸公南靖湖湘似卷云水,北尊天子如拱霄汉。美名光于史册,长策何其壮观!五段说:
“驱驰数公子,咸愿同伐叛。声节哀有余,夫何激衰懦?偏裨表三上,卤莽同一贯。始谋谁其间?回首增愤惋。”仇注解此段较切:“驱驰”,谓中丞遣使连兵。“数公子”,指裴虬、李勉、杨子琳。“上游”叙地,“端公”叙姓,于杨则隐讳其词,而归罪于偏裨。然曰“卤莽同一贯”,则杨当并分其过。曰“始谋谁其间”,则当时纵恶之罪,杨亦无所逃。钱笺:唐时藩镇有事,俱用偏裨将上表,假众论以胁制朝廷。《通鉴》谓杨子琳起兵讨玠,取赂而还。此咎其信偏裨之说而释兵不问。这段对杨子琳的讨玠取赂暗含愤慨:中丞您遣使联络诸公,大家都愿协同伐叛。风声节概,哀痛有余;竟使我也觉奋激,思自拔于衰懦。偏裨们再三上表,实则卤莽相同上下一贯。始约同谋讨贼,后来又是谁在挑拨离间?回过头来想一想,真教人顿增愤惋。末段说:
“宗英李端公,守职甚昭焕。变通迫胁地,谋画焉得算?王室不肯微,凶徒略无惮。此流须卒斩,神器资强干。扣寂豁烦襟,皇天照嗟叹!”《通典》:唐侍御史凡四员,内供二员号为台端,他人称“端公”。“李端公”,旧注皆云李勉,时在广州。勉本宗室,故有“资强干”之语。这段望济约勉以立功:李公是宗室的英俊,奉公守职政绩昭焕。要是他果能于贼党逼迫要挟之地而变通出奇,逆谋何得按原来的打算实现?他决不肯让王室衰微,而任凭凶徒肆无忌惮。(33)这种叛乱的逆流必须截断,支持社稷须赖本支中的强干。《文赋》说“叩寂寞而求音”,我今扣寂赋诗,一豁烦闷的胸襟;皇天当鉴临我的呼天嗟叹。老杜始终坚持他们房琯一派主张恢复分封制,以为“此古之维城磐石之义”“根固流长,国家万代之利”的保守想法(详第十五章第六节),这里又再一次得到表露。
臧玠之乱,史不详载。老杜亲身经历了这一兵变,且与杨济这样的封疆大吏有过接触,颇知内情,有所感发,作此数篇,犹如战地采访记,颇吸引人,亦富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相关阅读
文章标题:“杀气吹沅湘”-杜甫潇湘夕霁
链接地址:http://www.shootiniron.com/jianjie/914.html
上一篇:“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潇湘夕霁
下一篇:赞学与谢馈-杜甫潇湘夕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