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汉魏晋诗的三大传统之关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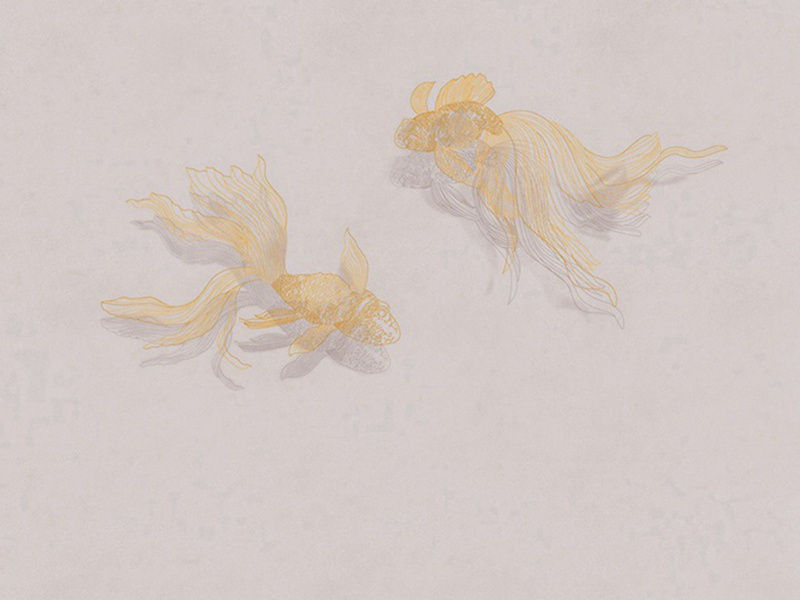
在后面四章,我们将集中讨论,杜甫与谢灵运、鲍照、齐梁诗人以及庾信之关系。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要说明,五言诗形成以后到谢灵运出现之前,也就是说,汉、魏、晋三代的诗歌传统。把这个背景分析清楚以后,我们才能适切地了解谢灵运、鲍照、齐梁诗人和庾信在其后的诗歌发展中的贡献与地位,才能适切地讨论他们与杜甫的关系。同时,在把汉、魏、晋诗整体地加以掌握之后,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杜甫与谢灵运、鲍照、齐梁诗人和庾信的传承关系特别重要,值得提出来单独讨论。
综合前人的看法,整个汉、魏、晋诗可以分成三个类别,或者说,三个小传统,即:乐府民歌传统,咏怀传统(以古诗十九首、阮籍、陶潜为代表),以及美文传统(以曹植、陆机、谢灵运及齐梁诗人为代表)。这三个传统并不一定同时存在,譬如,乐府民歌传统至晋太康时代逐渐汇入美文传统而丧失了独立的性格(详下),咏怀传统至陶潜而中断(详第二节),而美文传统则初起于建安(以曹植为代表),至南朝而一枝独秀;而且,这三个传统也并非完全彼此独立,譬如,建安诗歌就同时拥有三种传统的性格;不过,大致而论,这三个传统彼此之间有相当的独立性。至少,要了解汉、魏、晋诗的流变,从这三个传统的分辨出发,再来加以爬梳整理,并不失为历史研究的方便法门。
要分辨这三个传统的最好的起点是,把诗与乐府之间的界限划分清楚。就后代的眼光来看(特别是唐诗出现以后),这种区别已经不甚重要。譬如《唐诗三百首》虽然在每一体(五、七言古、近体)之后,都把原属乐府题的作品特别标明出来,但已经很少人去留意这种分类了。后代最重要的一部唐诗选集,沈德潜的《唐诗别裁》,干脆就只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五绝、七绝,而完全取消乐府这一类别。就唐诗而言,这种作法并无不妥之处。但在五言诗发展的初期,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乐府跟诗之间,是有体制上的区别之意义的。譬如在唐诗选里并不特别标举乐府的沈德潜,在论到早期五言诗时就会说:
《风》、《骚》既息,汉人代兴,五言为标准矣。就五言中较然两体:苏、李赠答,无名氏十九首是古诗体;《庐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类,是乐府体。
另外,王士祯在《古诗选》的五言部分也说:
乐府别是声调体裁,与古诗迥别。
沈、王两人都明白地提到“体”、“体裁”,可见在五言诗的早期阶段,乐府在“体制”上是与古诗迥然有别的。只是愈到后来,乐府愈是被吸纳到古诗之中,丧失了体制上的意义,后人也就逐渐忘掉了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特殊地位。不过,当我们谈到汉、魏、晋诗时,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记取这种区别,才能正确地理解早期五言诗的流变。
那么,乐府与古诗的区别何在呢?沈德潜说:
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
乐府宁朴毋巧,宁疏毋炼。
前者从音乐上说,后者从文字风格上说,但都比较抽象,难于掌握。至于王士祯,当学生问他:乐府与古诗何以有别,他答说:
古乐府五言,如《孔雀东南飞》《皑如山上雪》之属,七言如《大风》《垓下》《饮马长城窟》《河中之水歌》之属,自与五七言古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
这简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逃避之词,倒是张笃庆(历友)和张实居(萧亭)回答得比较具体。他们说:
盖乐府主纪功,古诗主言情,亦微有别。
乐府之异于诗者,往往叙事;诗贵温裕纯雅,乐府贵遒深劲绝,又其不同也。
为了比较和归纳,我们再把其他诗话中的一些看法罗列于下:
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徐祯卿《谈艺录》)
古乐府多俚言,然韵甚趣甚。(陆时雍《诗镜总论》)
古诗贵浑厚,乐府尚铺张,凡譬喻多方、形容尽致之作,皆乐府遗派也,混入古诗者谬。(施补华《岘庸说诗》)
综合以上的看法,我们可以说,古乐府(汉乐府民歌)至少有不同于苏、李诗和十九首的三点特色。首先,古乐府多叙事。这是很明显的,最有名的乐府诗如《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都是叙事诗;而以古诗十九首为首的正统的古诗,则尽量不叙事,或者尽量把叙事的成分加以压缩。其次,古乐府多描写,此即《岘庸说诗》所谓的“尚铺张”、“譬喻多方、形容尽致”,如《陌上桑》写秦罗敷的装扮云: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写人们见到罗敷的反应云: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像这样铺张描写、淋漓尽致的作法,在古诗十九首那一系统的作品里,总以尽量避免为宜;古诗以含蓄、比兴、情景交融为主。因此《岘庸说诗》会认为,这种作法“皆乐府遗派,混入古诗者谬”。最后,乐府的语言杂有相当成分的民间俗语,这就是《诗镜总论》所谓的“古乐府多俚语”,也就是为什么沈德潜认为乐府“宁朴毋巧,宁疏毋炼”的原因。譬如,相传为卓文君所作的《白头吟》: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
男儿重意气,何用刀钱为。
或者,又题为蔡邕所作的《饮马长城窟行》: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这都是脱胎于民间的语言与比喻的活泼生动的语句。而最早的“古诗”——古诗十九首,不论在语言上多么质朴自然,但从整体上看起来,总是以“雅言”为主的。至于后来的古诗系统的作品,那就更不用说,愈来愈文人化,愈来愈“雅”了。
其实,以上的说法还是比较传统式的,我们还可以用更现代的语言来分辨汉乐府民歌和古诗之间的区别。汉乐府民歌,按照民国以来的学者所说的,是属于民间文学、社会文学和写实文学的范围。它对一般人民的生活与感情有相当程度的反映,像《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和《孔雀东南飞》那样的作品,在五言诗逐渐文人化以后,的确是很少见的。它表达感情的方式,如《白头吟》的:
男儿重义气,何用刀钱为。
或者如《悲歌》的: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那种直截痛快的作风,和十九首以降的含蓄不尽、吞吐夷犹实在有很大的差别。
事实上,被传统列入乐府的作品,有些未必具有这种风格,反倒更接近文人化的五言诗,如《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不论就内容还是就语言来看,这都不是我们通常所意谓的乐府民歌。《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也是如此。反过来讲,不列入乐府,或不一定列入乐府的作品,有些在精神上倒是和乐府相近。前者如赵壹的《疾邪诗》:
河清不可恃,人命不可延。
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
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后者如《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等无主名的古诗。
我们可以说,在东汉末年五言诗逐渐趋于成熟的阶段,作品明显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具有鲜明的现实感,以相当民间化的语言描写当时社会的种种现象,常出之以叙事的方式。这就是传统所谓的乐府民歌。第二类也反映了东汉末年的乱象,但以感怀人生为主,比较不涉及具体的人民的痛苦,语言比较典雅(但还是保持质朴的风格),感情比较含蓄,这就是以十九首为主体的古诗。用现代的语言来说,第一类是社会写实诗,第二类是文人化的抒情诗。这两类的作品不一定可以截然划分清楚,但区别是有的。所以,在强调“辨体”的清代,王士祯和沈德潜等人都努力想要加以区分。只是他们拘泥于抽象的、形式的层次,不能从内容着手,尤其是不能从社会内容着手,因此一直不能分析得很清楚。
在紧接着而来的建安时代,这两类诗歌——这两个传统,还是并行而不悖。在写实诗方面,最伟大的作品当然是非蔡琰的《悲愤诗》莫属了,除此之外,较著名的还有曹操的《薤露》《蒿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第一首(步登北邙阪),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建安诗人在写乐府诗时,常常用旧题来歌咏时事,而置本意于不顾。如《薤露》《蒿里行》本是挽歌,曹操却拿来写汉末的乱事。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合后代所认为的正统乐府诗的写法,其实正保留了汉乐府的写实精神,和唐代杜甫、白居易的干脆抛弃旧题,“即事名篇”,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古诗方面,最能继承十九首传统的,当然是曹植的《杂诗》和《赠白马王彪》了。其余如曹操的《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曹丕的《杂诗》,也都属于这个系统。不过,曹操这两首诗的写实性较为鲜明,可算介于乐府与古诗之间。
到了正始时代,乐府与古诗的平行发展有了非常突兀的变化。就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两个诗人阮籍和嵇康所遗留下来的作品来看,阮籍完全不写乐府,嵇康也只有一首《秋胡行》(共七章);而这首《秋胡行》,也只是在题目上保留乐府的形式而已,就内容与风格而言,应该属于古诗。也就是说,写实的乐府传统,到了正始时代突然完全断绝。
接着而来的西晋,乐府似乎复兴起来了。当时最重要的三个乐府作家,就现存比较完整的作品来看,傅玄就有二十六首,张华七首,陆机则多至四十六首。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繁荣”。仔细分析起来,正可以从这些作品看出汉乐府民歌精神的消亡。这些乐府,事实上只是拟古。有故事性的,借古题咏古事,“所借为何题,则所咏亦必为何事”,不像建安乐府之借古题来叙时事。没有故事性的,借古题咏古意,“大抵就前人原意,敷衍成篇”。如果说,建安乐府继承了汉乐府的写实精神,那么,西晋乐府就开了后代拟古乐府的先河。
我们如果把陆机的拟古乐府拿来和他的拟古诗十四首比较,就更加可以看出西晋乐府的精神了。当陆机模拟十九首时,他对原作的题意与结构亦步亦趋;当他模拟古乐府时,他对乐府旧题的本事或本意也亦步亦趋。乐府跟诗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对陆机而言,他不过是在写甲类诗或乙类诗而已。
从此以后,乐府就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乐府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完全被吸纳到诗里去了。换成现代话来说,在五言诗的早期阶段,在汉魏时代,中国本来有一股强烈的写实诗潮流。然而,这个潮流到了正始和西晋以后,却几乎完全中断了。只有在刘宋时代的鲍照身上,我们才看到短暂的再现;只有到了唐代的杜甫,我们才看到这一传统重新被发扬光大。而这就是本系列研究的第四章“杜甫与鲍照”所要讨论的主题。
相关阅读
文章标题:杜甫与汉魏晋诗的三大传统之关系(一)
链接地址:http://www.shootiniron.com/jianjie/968.html
上一篇:杜甫与六朝诗人(三)